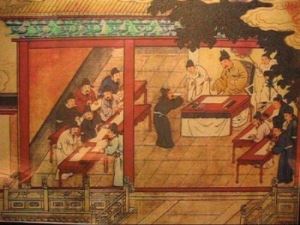拜占庭战神贝利萨留的晚年生活是怎样的?难道真的是在街头乞讨吗?

不过在公元548年的时候,贝利萨留离开了哥特的战场,回到了君士但丁堡。
在这之后他就慢慢的淡出了政治舞台。
很多人对他晚年的生活很是好奇,不过有传言说贝利萨留的晚年很悲剧,在街边乞讨。
那么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
【千问解读】
说起贝利萨留,相信了解欧洲历史的朋友们对这个人不会很陌生了,这是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战神,在他的率领下,成功的恢复了罗马昔日的光辉。
不过在公元548年的时候,贝利萨留离开了哥特的战场,回到了君士但丁堡。
在这之后他就慢慢的淡出了政治舞台。
很多人对他晚年的生活很是好奇,不过有传言说贝利萨留的晚年很悲剧,在街边乞讨。
那么这是真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贝利撒留回到君士坦丁堡后,鉴于自己的处境,选择了平淡低调的生活方式。
主观上,他多年来南征北战的事迹己经为国内外所熟知,成败自有评说,他本人对于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大可问心无愧,以乐观的态度来看甚至可以功成名就自居;从客观上说,岁月的流逝也令贝利撒留的心态和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血气方刚、一往无前的年轻军人,此时的他人到中年,不得不考虑个人的进退,自身的安危等现实问题。
况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已经明显失宠,查士丁尼一世似乎也找到了替代他的合适人选,贝利撒留这个时候无论愿意与否,只有一条路可走:隐退。
然而,贝利撒留毕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物,在为国家、为皇帝尽忠的同时,也并未完全忘记为自己的将来进行打算。
作为拜占庭帝国对外战争的一线指挥官,他在多年来同国内外敌人进行较量的过程中,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这些财富或多或少有一部分归于他个人私有。
查士丁尼一世对于他立下的赫赫战功也给予了不菲的奖赏。
贝利撒留本来便出身殷实之家,再加上他所获取的应得回报,必然成为富裕之人。
因此,他完全有理由有能力在人生的后半期尽享荣华富贵而不再卷入无谓的是非漩涡之中。

普罗柯比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及贝利撒留在各地的产业。
从他拥有七千人的私人卫队,能看出他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大批的启从,此外,他在君士坦丁堡市郊还拥有一处被称为潘泰希昂的领地,是通过继承得来的,由此也证实了斯坦霍普所推断的贝利撒留的贵族出身。
普罗柯比在该处明确写到,“到达拜占庭之后,他便在那里永久定居了,这时他已经积累了一大笔财产…”。
同样,《秘史》里也重申贝利撒留在东方掠取了大量财富,他在意大利战场更是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他的心己经完全为贪婪所占据”,后来狄奥多拉迫使其将三千镑黄金上交皇帝,理由是他将盖利默和维提却斯的财产据为己有。
而这些黄金仅仅是他家产的一小部分,其总数据称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不得而知。
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皇后以上的指控或普罗柯比的记载,可能带有虚假和夸张的成分,但贝利撒留晚年生活在物质上有足够的保障,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直到559年,一次突如其来的事件再次让他意外地重新披挂上阵。
这次事件主要由阿加西阿斯或迪奥法尼斯记载,当时贝利撒留还挂有帝国禁卫军司令的职务,突然传来蛮族军队渡过多瑙河大举南侵,兵锋己达距君士坦丁堡二十里处的消息。
时值寒冬,整个君士坦丁堡人心惶惶。
晚年的查士丁尼一世由于对军队的极度不信任,因而在首都布置的兵力极少,身边只有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神甫和学者。
贝利撒留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临危受命,他率领着匆忙征集起来的一千多人开赴前线,其老当益壮的无畏气概给予了市民很大激励,使得全城团结振奋,军民士气高昂。
贝利撒留一马当先,拜占庭军发起冲锋,首战就斩敌四百多人。
保加尔人为他的气势所震撼,很快撤兵,此后多年没有再度来犯。
贝利撒留拯救首都的大义之举赢得了万民欢呼,但查士丁尼一世却对他更加嫉恨,凯旋归来的贝利撒留在朝堂上只得到了一个冷淡的拥抱,之后皇帝便令他退到奴隶的行列中去。
击退保加尔人是贝利撒留人生的最后一战。
他不辱使命地为自己的军事生涯画上了句号,但吉本却认为,这次胜利带给他的只是一项罪名;斯坦霍普也表示查士丁尼一世对此不快。

关于贝利撒留终老的境况,约翰·马拉拉斯和迪奥法尼斯的编年史残卷中有真实记录,但这些内容却成为中世纪一直到近现代关于他个人的文学戏剧作品中最为令人感兴趣的部分。
史家可以证实的是,贝利撒留在562年卷入到一起谋杀查士丁尼一世的事件中。
当年查士丁尼一世因年老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久病未愈。
朝中重臣马赛卢斯和塞尔吉乌斯等人密谋用匕首行刺皇帝,但计划泄露,前者自杀,后者被入监拷问。
塞尔吉乌斯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供出贝利撒留的两名家臣,这两人为图自保,不惜卖主求荣。
563年12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贝利撒留仍被判处有罪,而查士丁尼一世为表示其“宽大与仁慈”,特许免他一死,代之以没收全部财产和终身监禁。
由于此案的不公难息众怒,次年查士丁尼一世终于同意为他平反,其自由和名誉得到恢复,财产也被部分归还。
565年3月,贝利撒留撒手人寰。
安东尼娜可能是看破红尘,将剩余的遗产全部捐出后,隐居修道院,直至去世。

尽管绝大多数史家相信,贝利撒留出狱后获得的补偿仍然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但文艺作品中却不约而同地将他的最后时光刻画得凄惨悲苦,颇具戏剧色彩。
传诵最广的说法是:贝利撒留在监牢被刺瞎双眼,出狱后也没有被返还财产,只得流落街头以乞讨面包片为生。
“赏贝利撒留将军一个便士吧”,这句话成为一句经典台词。
对此,历史学家们给予了一致的否定。
吉本指出,这些“毫无根据”的传闻来源于12世纪僧侣作家约翰·策策斯所编的一本《百科全书》,其中用十首民谣来描述贝利撒留的瞎眼和乞讨。
这个故事从希腊传到意大利,又被多人加工传唱。
然而策策斯的其他著作却明确否认了它的真实性。
斯坦霍普则专门用一节内容讨论了这个传说的来源和真假,他举出一些与此说法相似的史料,从而说明它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他本人也倾向于相信这个传说。

小编在此问题上有两点需要补充。
第一,关于贝利撒留瞎眼和乞讨的传说,有一个重要的媒介是19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罗伯特·格拉芙的剧本《贝利撒留伯爵》。
这部剧本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有关贝利撒留的文艺作品。
虽然其中引用了很多史料,且它的文学水平和艺术价值被公认为在19世纪的同类作品中首屈一指,但毕竟基于它剧本的特性,其中杜撰和改编的成分颇多,因而没有史学价值。
第二,几幅西欧启蒙时代晚期的名画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该传说起到了宣传普及的作用。

其中一幅是法国画家让·佛朗索瓦·皮埃尔·佩龙的《贝利撒留与农夫》,他所塑造的贝利撒留不是在乞讨,而是在关心救助穷苦的农夫,贝利撒留被置于阴暗的古建筑内,虽己沦落为民,但昔日的英雄气质犹存,他以同命相怜的心境关心着身边的人;另一幅则是拿破仑的御用画师雅克·路易·大卫的《贝利撒留在乞讨》。
画中一名妇女正向蓬头垢面、白发苍苍但仍身穿铠甲的贝利撒留施舍,而一旁的一个士兵却好像突然认出了昔日的老将军,举起双手呈惊讶状,画面极为细致传神。
这些画作更强化了贝利撒留晚年惨境这一历史传闻的戏剧性色彩。
无论如何,贝利撒留的晚年必定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
不过笔者相信,他的最终离去应该是有尊严的,当然也带着深深的遗憾。
圣像之殇:拜占庭帝国权力博弈下的文明裂变
这场披着宗教外衣的权力斗争,既是皇权与教权博弈的缩影,也是帝国在内外交困中寻求自救的极端尝试,其影响之深远,甚至重塑了欧洲的历史走向。
一、权力天平的倾斜:皇权对教权的终极压制 拜占庭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教会与皇权的矛盾早已埋下伏笔。
自君士坦丁大帝确立基督教为国教后,教会通过土地兼并与免税特权,逐渐成为“国中之国”。
至7世纪,教会掌控的土地已占帝国半壁江山,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越世俗政权。
利奥三世在726年颁布《禁止崇拜偶像法令》,表面以“偶像崇拜违背圣经教义”为由,实则直指教会权力核心——没收教会土地、强制教士还俗、关闭修道院,直接斩断教会的经济命脉。
这场运动将皇权推向空前高度。
不仅掌控宗教教义的最终解释权,更通过扶持“支持破坏圣像”的宗教势力,将东正教会纳入国家机器。
至843年运动终结时,教会已彻底沦为皇权的附庸,教皇国虽在支持下于756年建立,但拜占庭境内的教会彻底丧失独立地位。
这一转变,标志着中世纪欧洲“”模式的重大调整,也为后世“”理论的演变埋下伏笔。
二、帝国存续的代价:军事胜利与经济困局的双重悖论 在军事层面,破坏圣像运动曾短暂成为帝国的“强心剂”。
利奥三世利用东部军区对圣像崇拜的抵制情绪,将军事贵族与皇权深度绑定。
732年,君士坦丁五世在叙利亚前线大破阿拉伯军队,史载“士兵高呼‘皇帝即神明’,将缴获的圣物踩于脚下”。
这种将宗教狂热转化为军事动员力的策略,使帝国在8世纪中叶短暂收复小亚细亚部分失地。
但经济账本却揭示了运动的残酷真相。
教会土地的国有化虽短期内充实国库,却导致农业生产体系崩溃——修道院曾是农业技术的传播中心,其关闭使帝国丧失30%的葡萄园与橄榄园。
更致命的是,大量农民为逃避苛税涌入教会,运动强制还俗的20万教士中,仅15%重返农田,剩余者或沦为流民,或加入边境的斯拉夫雇佣军。
这种“”式的资源再分配,最终将帝国推向财政崩溃的边缘。
三、艺术革命的火种:从圣像禁锢到世俗觉醒 对艺术领域的冲击堪称颠覆性。
在君士坦丁堡,5500余所教堂的镶嵌画被石灰水涂抹,圣索菲亚大教堂内《基督变容图》的黄金底色被刮去,改绘为几何纹样。
这种暴力破坏却意外催生了新的艺术范式:修士们将圣经故事以连环画形式绣于丝绸,形成可移动的“行走圣经”;民间工匠转而雕刻动物纹样,诞生了“无脸天使”陶器——其翅膀以孔雀翎纹替代传统鸽形,象征世俗对神权的解构。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艺术中心的转移。
当拜占庭工匠因迫害逃亡意大利,他们带去的马赛克技艺与透视法雏形,直接发了威尼斯圣大教堂的建造。
而运动中形成的“反偶像”美学,更在阿拉伯世界催生出独特的几何装饰艺术——大马士革清真寺的星辰穹顶,正是拜占庭工匠在流亡中融合伊斯兰教义的产物。
这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为时期的人文主义埋下伏笔。
四、东西方教会的永诀:信仰分歧背后的地缘裂痕 运动期间,东西教会围绕圣像问题的分歧彻底公开化。
始终支持圣像崇拜,其传教士在运动高潮期甚至向君士坦丁堡走私圣像,导致787年尼西亚宗教会议将教皇使节逐出会场。
1054年的导火索,正是拜占庭皇帝以“支持破坏圣像”为由,拒绝承认罗马教宗的“普世牧首”地位。
地缘政治的博弈更令裂痕加深。
拜占庭为争取法兰克王国支持,默许其境内诺曼人劫掠南意大利的希腊教区;而罗马教廷则借助,将圣像崇拜与“正统信仰”绑定,形成“信仰即忠诚”的政治话语。
这种将宗教分歧武器化的操作,使地中海世界陷入“圣像派”与“反圣像派”的阵营对立,其遗毒至今仍在东正教与天主教的礼仪差异中可见一斑。
五、历史余波中的文明重构 当843年摄政皇后塞奥多拉宣布终止运动时,拜占庭帝国已。
皇权虽赢得对教会的绝对控制,却丧失了精神凝聚力——教会地产再分配催生的军事贵族,最终在11世纪演变为割据一方的“普罗尼亚领主”;而运动中兴起的民间艺术,则在14世纪与奥斯曼文化融合,孕育出独特的“拜占庭-伊斯兰”建筑风格。
这场运动更成为欧洲思想解放的隐秘推手。
当修士们被迫焚烧典籍时,圣凯瑟琳修道院的抄经人将著作混入《圣经》抄本,使新柏拉图主义在运动后复兴;而流亡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其携带的圣像破坏文献,更成为但丁《神曲》中“偶像批判”章节的灵感来源。
正如历史学家瓦西列夫所言:“破坏圣像运动既是中世纪的黄昏,也是文艺复兴的黎明。
” 在圣像的灰烬中,拜占庭帝国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完成了文明的涅槃。
这场运动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权力斗争的残酷教训,更是一个永恒的启示:当宗教沦为政治工具,其毁灭的不仅是神像,更是人类对神圣的敬畏;而真正的文明进步,永远诞生于对信仰的理性审视,而非狂热的破坏之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毁三观的古印度战神之车图片,外星生物飞船设计图纸曝光
古印度战神之车图片毁三观印度是一个宗教信仰非常发达的国度,这里有着无数的寺庙,在一座名为寺庙之城的地方,古印度战神之车图片的拍摄地点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地人称之为战车,战车上面刻画着许多神话人物,当地人并不是非常在意还以为就是神话传说中的东西,但是一分手稿却打破了这种观点。
这份用梵文书写的手稿,上面详细的介绍了关于古印度战神之车的结构,创造方式,所需原料,甚至是飞行员的训练方式都有清楚地记载。
并且文献多次强调飞船的顶部是金字塔形,顶端则是被透明的盖子所覆盖。
超级先进的飞船惊现史前印度为了验证这份手稿的真实性以及战车是否真实存在,多位研究者合作,按照手稿中的内容对战车进行了仿造。
仿造后的战车令研究者们大吃一惊,其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五千多公里,与其说是战车,不如说这就是古印度的飞船。
难道是外星生物隐居地球创造出来的飞船。
这架古印度战神之车已经装备有电子装置,避雷针,甚至还有喷焰式发动机,可以说这是需要现代的高科技水平才可以制作成功的。
可是相比于现代的科学技术,古印度还处于史前时期。
无论如何他们的科学技术都还未到达可以精准的制作出这样的飞船。
况且,他们当时的知识水平也不足以能够让他们正确的驾驶飞船。
那么,这个飞船是从何而来,或者说,古印度是如何制造这样的飞船呢。
战神之车是外星生物的座驾在印度这个地方.就有了飞船和飞船驾驶员,这样看来.人类的科技真像魔鬼一样奇怪。
当然,众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人类科技的进展是从当代和现代才开始的,那么.对古印度的飞船就只有一种解释看上去显得合理一点,那就是——这些飞船根本就不是人类所造。
也许那时的人们看到了一个这样的飞船,而这个飞船却是外星生物乘坐着到地球上来考察的,然后当地人根据这个也许被外星生物废弃了的飞船仿造出了其他的飞船,那些外星生物也便被他们当成了神仙一样供奉起来了。
也许,古印度根本没有修筑出这个“战车”,但是他们却通过某种途经得知了或者亲眼看见了这种飞船的创造方式,从而记录了下来,换而言之,古印度可能只是飞船的一个记录者而已。
所以飞船是外星造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