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起源时间是在哪一年是怎么回事?荷马时代简介

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盲
【千问解读】
这一时期的历史主要是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史诗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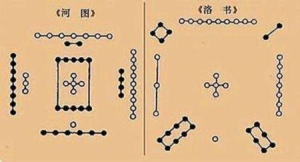
形成于此时的“”叙述了迈锡尼文明的旧闻,但又表述了当时社会的情况,故又称此时代为“荷马时代”,也称“史诗时代” 起源 荷马时代(约前1100年至前800年)指的是希腊历史中从多利亚人入侵及迈锡尼文明灭亡的公元前十二世纪直到公元前九世纪最早的希腊城邦之崛起时期。
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中记录的便是这段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为《木马屠城记》。
迈锡尼文明的没落在时间上对应于数个近东帝国的衰落,特别是和埃及新王国的衰落,其原因可能为某个装备有铁兵器的“海上民族”的入侵。
当多利亚人南下希腊的时候,他们也装备有更为先进的铁兵器,可以轻易地将已然衰弱的迈锡尼人消灭。
这之后的历史时期被古希腊诗人荷马后来记录在自己的诗集《伊利亚特》及《奥德赛》之中,故统称为“荷马时代”。
学显示出希腊世界在这一时期中文明的衰落,迈锡尼人雄伟的宫殿被摧毁或是遗弃,希腊语停止被书写。
荷马时代的陶器只有简单的几何装饰,缺乏迈锡尼文明期间的器件所展现的丰富的图案设计。
荷马时代的希腊人的居住点数量稀少,并且规模很小,可能说明人口的急剧减少。

没有发现产自国外的货品,可能表示国际贸易的丧失。
同时,与其他文明的联络也消失了,导致社会文化等的全面倒退。
社会制度 政治 荷马时代的多利亚人没有建立国家,尚处于军事民主制度时期,这一时期的多利亚人部落有议事会、人民大会、军事首领三种机构。
议事会由各个氏族部落的族长组成,后来成为全体氏族贵族的会议,重大问题皆须经此议论然后通过,最后提交人民大会表决;人民大会则是由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成年男子组成,原则上是部落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军事首领(古希腊语称“巴赛勒斯”)是由人民大会选举而出的军事领袖,主持祭司和诉讼,战时出征。
随着后来多利亚人的经济不断的发展,议事会和军事首领不断的变为世袭工具和权力机关,标志着荷马时代的氏族制度的逐渐解体。
经济 荷马时代的多利亚部落的生产力开始发展,出现了铁器,在农业上,繁复的农业用具和双牛犁已经出现并使用;三耕法和天然肥料也开始广泛使用;各类家畜也已经由专人饲养。
手工业也开始和农业分离,出现了陶匠、木匠等分工。
商业交换也开始发生,以物物交换为主,用铜、铁、牲畜或皮革进行交换。
奴隶制度 荷马时代,由族部落的解体,农村公社(即与我国建国初期相仿的制度),这一文明退化的象征开始建立在古希腊地区。

接着,公社的土地开始划分为小块份地,氏族贵族则占有庞大的土地和牲畜,而普通的农村公社成员则沦为雇工甚至乞丐。
奴隶制度也在此时开始出现,主要是战俘,男奴进行放牧,女奴进行家务劳作,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消亡 多利亚人部落经济的发展,使得多利亚部落开始解体,国家开始逐渐形成。
进入公元前8世纪后,铁器在古希腊社会广泛的使用,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人口的增多,使得古希腊人开始在小亚细亚、爱琴海、地中海地区进行殖民。
在这一时期,商人出现,各个地区开始形成城市和商业中心,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开始形成。
至公元前8世纪至6世纪,希腊各地产生了200多个城邦,荷马时代就此结束。
由于这个时期的繁荣度有类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和克里特文明时期,故又被史学家称为“”。
随机文章汉景帝和亲政策对汉武帝的影响?楼兰遗址为什么不能去,极其危险千万别去(天价门票3500元)蜥蜴人的真相是什么,疑似外星生物/传闻创立地球最强组织被加蓬蝰蛇咬了有救吗,有救/但被咬的部位100%会被截肢中国第一神山昆仑山为什么驻军,昆仑山出现虫人/巨兽/死亡禁地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