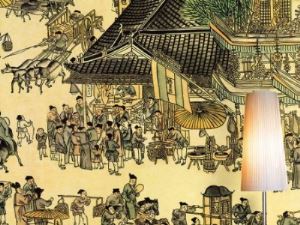唐代陌刀当作一件威力之强的神兵 为什么到了宋代却销声匿迹了

回首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战争是其中一个留下浓墨重彩的主题,伴随战争而诞生的兵器在那
【千问解读】
回首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战争是其中一个留下浓墨重彩的主题,伴随战争而诞生的兵器在那个战事频繁的年代也就尤为重要。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记得先人许多神兵利器的名字,特别是威力殊绝的大型重武器,即使只看过一眼都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秦强弩、汉环首刀、宋布人甲等,即使是今人也耳熟能详。
但我国的顶峰大唐,与它赫赫武功伴生的一件神兵却少为人知,这种兵器就是唐陌刀。
陌刀是一种长柄刀,唐代的陌刀本是由汉代的战马刀演变而来,并且较汉斩马刀发展出大不同,陌刀双刃、长丈余,威力极大,在唐代时以及成了部队克星的存在。
它刀脊厚实,使武器斩击的冲力大大加强,不同于一般刀剑类武器破甲能力弱,陌刀的斩击破甲效果极佳。
如果说在的相当于现代战争中的坦克,那么陌刀就是反坦克炮,大唐的步军就是这种威力无比神兵的加持下,击败东,赢得。
在正史记载中,也不乏陌刀的身影。
在公元621年,唐军将领阚棱曾亲持陌刀带领千余步兵在同割据军阀的对决中发挥出彩表现,史称阚棱每一举刀,辄毙数人,前无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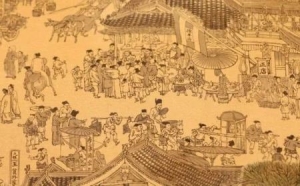
短短数语,足见其时其人其刀之威风,当之者无不披靡。
这是在大唐开国早期陌刀的一次表现,在中后期亦不乏陌刀的神来之笔,在差点颠覆大唐的大变中,陌刀再一次为大唐立下。
大唐名将李嗣业,他曾任怀州刺史、北庭行营节度使,爵虢国公,但真正使他天下闻名的还是他的一手陌刀功夫。
据正史记录,嗣业身高七尺,力大超群,好使陌刀,逢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即使敌军也拜服尊称其为“神通大将”。
在具体战役中,李嗣业的巅峰是收复长安之战。
当是时,唐军在长安城西沣水东岸结阵,而十万叛军在北聚集,叛军贼首李归仁率精锐铁骑兵出阵挑战。
唐军以弓弩射击意图打散叛军队形,而后派骑兵正面突击,逼近叛军中军,但叛军一齐反扑,唐军反退,叛军乘机全军追击,唐军惊乱,阵型大坏。
这时李嗣业卸甲袒身,手执陌刀,立于阵前,怒声大喊,奋勇杀贼,当其刀者人马俱碎,一连被斩数十人,叛军为之一滞,这时唐军稳住局面,然后李嗣业率领前军两千步兵各持长刀、长柄斧,横队如墙向前猛攻,最终。

凡此几例,即可看出唐代陌刀之凶悍、神勇,然而这样的神兵却没有流传到后代,在宋时就渐已销声匿迹。
陌刀失传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是造价高昂、技术失传,“夹刚”、覆土烧刃等工艺使成本居高不下,而一些更为特殊则随着唐代军营中的工匠一齐消逝了,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历史莫大的损失和遗憾。
其二在于陌刀对使用者要求过高,唐代的陌刀手首先要是严格精选的壮士,不仅需要刀法娴熟,还得胆气十足、臂力过人,不然即使有刀舞不起来也是徒劳。
而这些要求的实现在重文轻武以致社会整体文弱的社会更显困难。
除此外,当时官府严禁民间私藏兵器,更不用说陌刀这种大杀器了,于是不久陌刀终于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巨型欧肯纳根水怪高达150米,印第安人当作神兽来祭祀
但是有一只水怪却让人不可思议,它就是欧肯纳根水怪。
因为很多目击过这只水怪的居民,都会认为这就是中国真龙。
中国的水怪是相当多的,但是加拿大则与中国不相上下。
在世界水怪排名上,加拿大就有两个水怪荣获上榜,它们是尼斯湖水怪和欧肯纳根水怪,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这个欧肯纳根水怪,巨型欧肯纳根水怪高达150米,被印第安人当作神兽来祭祀。
欧肯纳根水怪有不少人曾经见到过这个欧肯纳根水怪,说起这个水怪,它的样子就好像是中国的龙一样。
不管是角和身躯,都跟中国传说中的龙一样。
它的体型也是很很大,目击者称这个巨龙的长度达到60米,如果伸直的情况下,这条水怪可以达到150米。
对于以中国龙为神明的人们,往往都会认为这是神灵,并不是什么怪兽。
印第安人当作神兽来祭祀欧肯纳根是加拿大有名的地方,这里的山和水都是世界有名,更是得到大众的喜欢。
尤其是这里的湖水,早在石器时代就存在,更是被人们认为深藏着水怪。
不过这个水怪被人们当做神明一样的供奉。
本来加拿大的土著居民也对这个水怪的传说很是相信,这里的印第安人将水怪当做神兽一样的对待。
每隔一定的时间,或者特定的日期,印第安人总会拿出一些物品来祭祀水怪,这些祭祀的物品就是各类小动物。
他们这样去祭祀水怪的做法,本来就是祈求平安。
对于欧肯纳根水怪潜藏在哪里,很多印第安人会对此作出这样的回答,他们说这个水怪会深藏在湖底的深洞穴中。
印第安人则会利用小舟将动物带给怪兽。
说到这个欧肯纳根水怪,它的很大体积和酷似中国龙的外形,博得了很多人们的关注。
但这水怪是真是假?恐怕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真的证实。
乱世才媛的悲歌:唐代女诗人李季兰的命运浮沉
这位六岁能诗、一生困于情海的才女,其人生轨迹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盛唐气象下女性文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突围。
一、诗才惊世:被父权阉割的童年 李季兰(713-784年)本名,字季兰,乌程(今浙江湖州)人。
其幼年显露的文学天赋,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异化为命运的诅咒。
六岁时作《蔷薇》诗:“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以“架却”谐音“嫁却”,暗喻待嫁女子心绪纷乱。
其父身为地方,却将女儿的诗性觉醒视为洪水猛兽,断言“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遂将其送入剡中玉真观出家。
这种以“净化”为名的放逐,实则将女儿推向更复杂的社交场域——唐代道观常为文人雅集之地,李季兰在此接触朱放、皎然、等名士,其诗名与绯闻齐飞,终成“风情女子”的标签。
二、情路迷局:在礼教与自由间的撕裂 李季兰的情感世界,是唐代女性突破礼教桎梏却难逃悲剧宿命的缩影。
她与诗僧皎然的交往最具典型性:皎然以“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的决绝,拒绝了这位“才貌过于须眉”的女冠求爱。
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克制,实则是教界对世俗伦理的妥协——彼时玉真观虽为女冠聚居地,却因、等皇室女冠的私生活争议,导致朝廷多次整肃。
李季兰对陆羽的“友达以上”之情,亦因二人自幼相识的兄妹情谊、陆羽弃婴出身导致的门第差异而止步。
这种情感困境,恰如她在《八至》诗中所叹:“至亲至疏夫妻”,道尽女性在爱情与婚姻中的被动处境。
三、名士交游:才情背后的政治风险 李季兰的诗名与社交圈,使其成为中唐政局波动的敏感符号。
她与茶圣陆羽、诗人刘长卿等名士唱和,其诗会规模甚至扩展至广陵(今扬州)。
这种跨阶层的文化互动,在后被政治化解读。
建中四年(783年),朱泚称帝长安时,李季兰因与其诗书往来遭迁怒。
德宗斥责她“何不学严巨川作诗‘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最终以“扑杀”处决。
这场悲剧暴露出唐代女性文人的双重困境:她们既享受着的文化红利,又因性别身份无法进入权力核心,最终沦为政治清算的。
四、诗名永驻:在文学史中的突围与重构 尽管史书对李季兰的记载仅存吉光片羽,其文学成就却获得后世高度评价。
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赞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刘长卿更以“女中诗豪”称之。
其代表作《八至》以辩证思维解构世俗伦理,在哲学深度上超越同时代男性诗人;而《送阎二十六赴剡县》中“流水阊门外,孤舟日复西”的意境,则展现出女性视角的苍茫时空感。
这些作品在被收入《唐女郎诗集》,与、鱼玄机等人并称“唐代四大”,实现了从个体悲剧到文学经典的升华。
五、文明镜像:女性话语权的千年回响 李季兰的命运,是唐代女性文人群体困境的缩影。
她们虽享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却始终无法突破“才女—情妇—祸水”的叙事窠臼。
称帝带来的女性政治空间扩张,并未惠及底层文人女性;中晚唐与,更使文人群体整体边缘化。
李季兰的悲剧,本质上是传统社会性别秩序与政治动荡共同作用的结果。
她以诗笔为刃,在“至亲至疏夫妻”的悖论中,刺破了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其“扑杀”结局,则成为皇权对异己话语最暴力的规训。
在湖州故里的荒冢前,那方被风雨侵蚀的墓碑,恰似文明长河中的一枚时间琥珀。
它封存着一位女性在礼教与自由间的挣扎、在爱情与政治中的迷失,更见证着中华文明对女性话语权的漫长探索。
当我们在数字化时代重读《八至》,李季兰的叹息依然穿越千年时空,叩击着每个时代对性别平等的思考——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给予女性多少自由,而在于能否让每个灵魂都拥有书写历史的权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