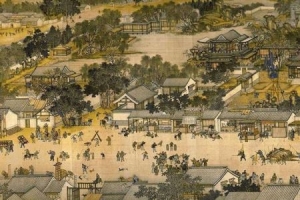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有哪些?他们为蜀汉带来了什么?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小编一起看看吧。
蜀汉的终章充斥着投降与牺牲,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蜀汉亡国之际,力主
【千问解读】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跟小编一起看看吧。

蜀汉的终章充斥着投降与牺牲,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蜀汉亡国之际,力主投降以及阵前叛变的多为益州势力人物,而在一线为蜀汉政权存亡拼尽最后一丝力量的却多为外附势力以及蜀汉元勋的后代。
一、武人居多 1. 投降者的分类 蜀汉政权中的外附势力官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战争中归降的敌对势力官员,另一类则是主动依附、投奔蜀汉的文武官员。
这其中以前者的数量更多,如是刘备入蜀时投降的原手下,王平是汉中之战时收降的曹魏将领,申耽、申仪在刘备进攻上庸时归降,南征时收降孟获、孟琰,第一次北伐时又在天水收、梁绪、梁虔、尹赏四人,时期也有收降郭脩一事。
这些在战争中投降蜀汉的官员,除刘巴是势力灭亡而降的文官外,其余大多是掌管一定军务的中低层武将,这也是蜀汉中后期收降人才的主要来源。
另一类主动归附的官员同样也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这其中既有、雷绪这种早期携部曲来投的案例,又有、这种成名武将远投蜀中的例子。
与前面的降将们不同,这种主动依附的武将级别往往会更高。
2.以武人为根基 蜀汉政权外附势力之所以会呈现出武将居多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政权本身所存在的武人倾向决定的。
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但其早年生涯艰辛更近乎于下层平民。
这样的一个势力对世家大族出身的名士们吸引力不大,因此外附势力武人居多是有其先天因素的。
刘备虽然从客居荆州时期就开始有意识地调整人才方针,广交荆襄大族,但是当时中国主流的文化重镇在江北的中原大地,绝大部分的人才都聚集在中原,渴望为皇室正统效力。
诸葛亮在隆中隐居之时,与石韬、、孟建相善,这三人也是在时任荆州牧广招人才政策下客居于此的名士。
诸葛亮出仕刘备时,这三人并未一同为刘备效力。
孟建“思乡里,欲北归”,徐庶、石韬二人也在南下时“俱来北”。
在那个时代的潮流下,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无疑是大部分世家大族的头号选择,其次是“招延俊秀,聘求名士”的江东孙家,最后才会轮到军旅出身的刘备阵营。
之后篡汉,绵延四百年的汉家皇室大旗轰然倒塌,新生的曹魏政权的政权合法性受到了广大士人的质疑,当时已经即位汉中王的刘备本已迎来人才争夺战中的绝对良机。
然而由于他不顾刘巴、雍茂等人的劝谏急于称帝,并且还“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此后,魏、蜀、吴三国格局趋于稳定,各国基本上都只能在本国领土上招揽人才。
领土最小、仅有一州土地的蜀汉人才选择面最为狭窄,于是在对外征战的过程中尽量俘虏、招降人才就成为了蜀汉仅有的扩大人才源的途径。
由于在战争中能够收降的人才多是武将,这直接决定了外附势力多为武将的特点。
二、官爵颇高 1.千金买骨 由于蜀汉政权在吸引人才方面既没有名义上的优势,又在地理因素上存在,因此刘备、父子在人才引入上花了不少心思。
其中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对于远投蜀汉政权的敌国文武,蜀汉方面不惜以高官厚禄来拉拢人心,颇有千金买骨的意味。
刘备在其执政时期,对于外附势力中拥有相当声誉的人士,往往会任命其为政权内部的高级官员,这其中最明显的两个案例便是马超与刘巴。

建安二十年,马超刚刚依附便被任命为平西将军,四年后升左将军。
之后,马超更是“迁,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并且还将马超之女配与安平王,刘马两家结为亲家。
无论是升迁速度还是官职地位,马超都堪称刘备时期的武将第一人。
刘巴虽然与刘备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才智绝人”被世人称为高士的他也仍旧成为了继之汉的第二任尚书令。
后主刘禅时期,蜀汉延续了之前的人才策略,继续以高官厚禄笼络降人。
且不论王平、姜维这些才华出众的外附势力代表,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与姜维一同归降蜀汉的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人,最后也分别官至大鸿胪、、大长秋。
此三人在史书之中并未见其他记载,也未见其有何特殊才干,但是却由时期的佐吏身份最终成为蜀中两千石级别的中高级官员,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蜀汉高官厚禄的人才吸引策略。
2.人才换代 三国后期,各国趋于均势,蜀汉政权内部老一代出身于北方诸州的人才纷纷病逝,新一代人才只能局限于荆益二州人士,在人才的更新换代上出现了一定的断层,于是蜀汉对待降将的待遇就越来越高。
延熙十三年,姜维出兵西平,擒获魏西平中郎郭脩,据《春秋》所载,郭脩在降蜀之后“刘禅以为左将军”,郭脩由中郎骤升至左将军,这样的跨度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且左将军一职于蜀汉有着特殊的意义,刘备早年被封为左将军,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世人言及左将军皆指刘备。
蜀汉立国以来,被封为左将军的官员中可考的共有五人,除郭脩之外其余四人分别为马超、吴壹、向朗、句扶。
这四人中马超、吴壹是久经沙场的,句扶是能够与王平相提并论的益州大将,向朗则在诸葛亮去世后一度代理过丞相一职。
郭脩虽然“素有业行,著名西州”,但是一朝之间位居要职,蜀汉外附势力归附以来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三、朝中话语权有限 虽然以马超、刘巴、魏延、姜维等人为代表的外附势力在蜀汉政权内部官爵颇高,但他们在朝中却未拥有与他们官爵相匹配的政治话语权。
外附势力多为敌国降将,为了表现出、渴求人才的态度,刘备、刘禅父子愿意给予高官厚禄的物质封赏,但是具体到实际政治权力上,外附势力则没有太多插手的空间。
像马超这样“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且“信著北土”的前割据军阀,对刘备势力而言形如鸡肋。
马超若肯安心为其所用,对于刘备的民族战略大有裨益,且马超代表的西凉马家也算是一方豪族,能够极大程度提高刘备阵营的知名度。
但由于马超素有反复之名,因此刘备并不敢放手任用马超,他只是将其置之于殿堂之上,徒借其名而已。
形容汉中的那句“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用在马超身上也很是贴切。
与马超相比,同时期的刘巴并没有马超那么大的威胁,但是作为蜀汉开国以来的第二任尚书令,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刘巴在这一要职上有何表现,刘巴在任时的所有工作似乎只有撰写“诸文诰策命”。
在刘备执政时期,由于君主不信任加之元臣宿将俱在,外附势力根本不具备争夺政治话语权的条件。
此后的魏延、王平等人,虽然都坐镇于汉中战场一线,掌握一定的军权,然而他们都属于社会出身较低,毫无政治威胁的纯军事型人才。
即便时人多以为魏延会成为诸葛亮去世之后的接班人,但他当时也只是在军事层面上有些许权力,在朝中却毫无影响力可言。

直到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面临着人才断代的问题,以诸葛亮弟子身份在蜀汉朝中平步青云的外附势力代表姜维才终于加入到了蜀汉政权内部的最高决策层中。
可是“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
祗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常年征战在外的姜维难以顾全朝中,以至于影响力远不及前人。
外附势力尴尬的定位决定了他们难以在政权中获得足够的权力,在蜀汉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国家内,旧有的权力结构就更加难以打破,此时留给外附势力的权力就很有限了。
四、政治斗争能力不足 主要以武将为主的蜀汉外附势力在复杂的势力之争中肯定不如在战场上厮杀那般得心应手,外附势力应付政治斗争的能力普遍不足。
这里所说的政治斗争能力不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主观意识上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二是本身能力不足以应付政治斗争能力。
前者主要是像刘巴、马超这样名望颇高的文武官员,他们因为其自身原因有着各种顾虑,因此更愿意明哲保身而非加入到荆襄势力与东州势力的政治斗争之中。
更多的外附势力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魏延、姜维尤为典型。
时期,魏延是蜀汉军中的头号大将,他常常希望能够代替诸葛亮率军北伐,但他性格高傲,导致“当时皆避下之”。
此外,他还与属于荆襄势力的势如水火,这些无谓的争执不断地败光了自己的政治资本。
魏延最致命的失误在于诸葛亮逝世时,他面对诸葛亮中意的二号接班人说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
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
这番话一来表露出魏延试图把持军权而丞相府旧臣必须放弃军权回朝治丧的意思,二来得罪了其他敬仰诸葛亮的中立人士。
不经斟酌的一番言语,最后导致杨仪在诬告魏延谋反时“琬、允咸保仪疑延”。
朝中没人为他说话,而掌握蜀汉大军的又是长久以来的仇敌杨仪,魏延离三族被夷的下场也就不远了。
曾与魏延一起并肩作战的姜维在自己爬上大将军的高位后也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与魏延不同,姜维从性格上来说并没有像魏延那样明显的性格缺陷,他的为人反倒得到时人不少的赞许。
姜维在这样的情况下仍陷入政争漩涡之中,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所处的时代正是蜀汉政权中比较尴尬的一段时期。
结语 在蜀汉最后的岁月中,第二代荆襄、东州势力代表纷纷离世,新一代接班人试图抢班夺权,益州本土势力蠢蠢欲动,而这一切影响因素都集中作用于姜维身上。
姜维虽然屯田沓中躲过了等人的暗算,但是黄皓姜维交恶、主力大军远屯沓中的结果最终还是反噬了蜀汉自身,姜维这仅有的一次错误直接影响了蜀汉最终的国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孤舟浮江,诗心映世:马周诗句中的寒微之志与家国情怀
这位以政论文章闻名史册的能臣,仅存的两首诗作却成为解读其精神世界的密钥,在山水意象与人生哲思间,勾勒出初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孤舟映日:寒微境遇中的诗意突围 《凌朝浮江旅思》开篇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 ,以晨曦初照、孤舟漂流的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羁旅图景。
这种 孤舟 意象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马周早年困顿生活的隐喻——他出身清河茌平寒门,少孤贫而好学,精研《》《春秋》却久困场屋。
诗中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的视觉错位,恰似其怀才不遇的生存困境:远山隐于雾霭,暗喻仕途渺茫;潮水看似凝滞,实则暗涌流动,隐喻着诗人内心对机遇的渴望。
这种寒微书写在 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 中达到极致。
花开花落的瞬间轮回,与江鸟沉浮的动态捕捉,既是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更是对人生无常的哲思。
北宋张耒在《马周》诗中 布衣落魄来新丰 的描述,恰与此诗的孤寂意境形成互文,共同勾勒出寒门士子在盛世中的精神困境。
二、邓林栖枝: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 马周现存另一残句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虽仅十字却振聋发聩。
此句化用《·逍遥游》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的典故,却翻转出新的意蕴:当邓林(神话中昆仑山神木)般的机遇近在咫尺,诗人却选择 不借 的傲骨。
这种选择绝非消极避世,而是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精神突围——贞观十一年,他以《陈时政疏》直谏唐太宗 积德累业,恩结人心 ,展现出比借枝栖息更深远的政治抱负。
这种精神特质在《凌朝浮江旅思》的结尾 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 中得到升华。
面对千里羁旅的哀愁,诗人选择以诗长歌消解,而非攀附权贵。
这种 不借枝栖 的独立人格,与同时代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的悲愤形成对照,更显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三、政论诗心:双重文本中的士人担当 马周的诗歌与其政论文本构成奇妙的互文关系。
在《陈时政疏》中,他痛陈 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 ,这种以民为本的忧思,与《凌朝浮江旅思》中 羁望伤千里 的悲悯一脉相承。
其政论文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 的论述,恰可视为 长歌遣四愁 的另一种表达——将个人愁绪升华为家国担当。
这种双重文本的创作特征,在初唐文人中颇具代表性。
马周既能在《请劝赏疏》中提出 劝农务本 的具体政策,又能在诗中保持 岸花开且落 的审美距离,这种 入世 与 出世 的平衡,使其成为研究唐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典型样本。
四、历史回响:寒微之志的永恒示 马周诗句在后世文人中引发持续共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的禅意,与 潮平似不流 的静观哲学遥相呼应;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超脱,暗合 长歌遣四愁 的精神境界。
这种跨时空的共鸣,源于寒微文人共通的生存体验——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在困顿境遇里坚守理想主义。
在当代语境下,马周诗句的价值更显珍贵。
当现代人面对 内卷 困境时,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的傲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坐标;当社会焦虑蔓延时, 岸花开且落 的哲学思考,为浮躁心灵注入清凉剂。
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经典诗歌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
从孤舟漂流的寒微书生到位极人臣的贞观,马周的人生轨迹恰似其诗句的双重变奏——既有 春水送孤舟 的凄清,亦有 一语君王见胸臆 的豪迈。
他的诗句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文学注脚,更是初唐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镜像。
当我们在苏州河畔诵读 太清上初日 时,听到的不仅是千年前的江涛拍岸,更是一个时代寒微之士的灵魂回响。
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或许正是诗歌给予文明最珍贵的礼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魏丑夫:战国权力漩涡中的男宠与人性博弈
魏丑夫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被明确记载的男宠,其人生轨迹与秦的政治生涯深度捆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
一、身份谜团:从市井到宫廷的逆袭 魏丑夫的出身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
据《》记载,他可能是流亡贵族后裔,或仅为咸阳城中的落魄书生。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因长相酷似宣太后年轻时的初恋情人,被作为政治工具献入宫廷。
这种 替身文学 的设定,既符合战国时期宫廷斗争的残酷逻辑,也暗合宣太后对情感慰藉的深层需求。
在执政晚期,魏丑夫以 侍从 身份进入宫廷,凭借精通音律与善解人意的特质,迅速获得太后宠信。
其从市井到宫廷的跃升,既得益于个人才貌,更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对男性美色的特殊审美——不同于后世对男宠的贬低,战国贵族更看重其文化素养与情感共鸣能力。
二、权力棋局:男宠与太后的共生关系 魏丑夫与宣太后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情感依赖。
在秦昭襄王早期,宣太后通过 四贵 (、、公子悝、公子芾)掌控朝政,魏丑夫作为 隐形第五人 ,实则扮演着权力缓冲器的角色。
他既不参与核心决策,又能通过情感纽带消解太后的政治焦虑,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其在宫廷斗争中得以自保。
宣太后对魏丑夫的宠爱达到何种程度?史载其晚年将私库钥匙交予魏丑夫保管,甚至允许其参与部分外交礼仪。
这种超越常规的信任,既源于太后对青春情感的追忆,也包含着对权力延续的隐喻——当魏丑夫穿着象征秦国最高礼制的玄端服侍奉太后时,其身份已悄然从男宠转向权力符号的具象化载体。
三、生死博弈:殉葬风波中的政治智慧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宣太后病危时下令 以魏子为殉 ,将这段关系推向生死考验。
这道殉葬令背后,实则暗含三重政治逻辑:对魏丑夫过度干预政务的警告、对先王的赎罪仪式,以及通过极端手段巩固太后权威。
魏丑夫的绝地反击堪称经典政治博弈。
他通过谋士提出 人死无知 与 先王积怒 的双层逻辑,既利用战国时期流行的无神论思想动摇太后决心,又以孝道伦理迫使太后让步。
这场对话本质上是新兴思想与传统的交锋,庸芮 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久矣 的诘问,实则暗示宣太后若执意殉葬,将动摇秦国 以孝治天下 的立国根基。
四、历史镜像:男宠现象的文化透视 魏丑夫现象绝非孤例。
将之与同时期与的组合对比,可见战国男宠的两种典型模式:嫪毐代表政治投机型,最终因觊觎王权而覆灭;魏丑夫则代表情感依附型,通过精准把握权力边界得以善终。
这种差异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对男宠的双重期待——既是情感寄托,更是权力游戏的参与者。
从文化史视角审视,魏丑夫的存在挑战了传统性别秩序。
在男权主导的战国社会,宣太后公开豢养男宠并赋予其政治影响力,实则是女性统治者对性别压迫的隐性反抗。
这种 以男宠制衡男权 的策略,与后世设置 控鹤监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五、余音绕梁:历史评价的维度重构 后世对魏丑夫的评价长期陷入道德批判的窠臼,但若置于战国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其存在价值远超 男宠 标签。
他既是宣太后情感世界的投射载体,也是秦国权力结构的润滑剂,更是研究战国性别史与政治文化的重要标本。
在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坑中,学家发现多具青年男性骸骨与女性贵族合葬,这种 反传统殉葬模式 或许正是宣太后-魏丑夫关系的物质遗存。
它提示我们: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需要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转而关注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逻辑与文化意义。
魏丑夫的人生轨迹,恰似战国权力棋局中的一枚特殊棋子。
他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又在不经意间改写了历史走向。
当后世学者在竹简残片中拼凑其人生碎片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男宠的,更是一个时代对权力、情感与生死命题的终极叩问。
这种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对话,或许正是历史研究最迷人的魅力所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