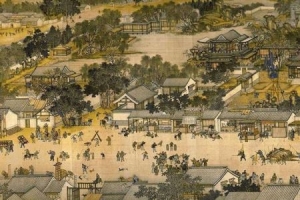解密鲁迅之死:或可能被日本军医谋害致死?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
【千问解读】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

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
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
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
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
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
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
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 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
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
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 》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
鲁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复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凉,终至大病,卧不能兴者匝月,其间数日,颇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连日记都停笔了,至三十日才又续记。
所以说“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
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
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
”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
……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
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
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
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
离东京近,就不好。
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
那时再看罢。
”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
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
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
”治疗暂告一段落。
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
”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
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
”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
”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
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

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
”治疗又告一段落。
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
”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
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
衡体重为三八.七罗格兰,即八五.八磅。
”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
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
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
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
”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
……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
”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
鲁迅去世后不久,黄源在《鲁迅先生》一文(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与此正相符合:“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他本想七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去养病。
起初想到镰仓,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绕缠。
后来想到长崎,有一天我去,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
但在长崎没有熟人,他觉得住Hotel太贵,住‘下宿’或租‘贷家’又太麻烦。
‘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指家里的人)当翻译了。
’他说。
‘我想告雨来帮忙吧,她暑假里在东京反正天热,不读什么书,有些事情她可帮许先生应付。
’我说着。
……‘不,她从东京赶去路太远,过些时再说罢。
’他婉辞谢绝了。
”所提到“雨”即许粤华,笔名雨田,黄源当时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学。
八月七日,鲁迅致曹白:“我还没有走,地点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诉人,因为每人至少总有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对他说,那么,给一个人知道,数天后就有几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况上,颇不方便。
信件也不转寄。
一者那时当停止服药,所以也得更减少看和写;二者所住的地方,总不是热闹处所,邮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
”同日致赵家璧:“我的病又好一点,医师嘱我夏间最好离开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说不定。
”但就在这一天,日记云:“往须藤医院,由妹尾医师代诊,并抽去肋膜间积水约二百格兰,注射Tacamol一针,广平,海婴亦去。
”自此先是须藤助手钱君,继而须藤自己每日来注射,鲁迅又复“不能离开医生”了。
八月十三日,鲁迅致沈雁冰:“说到贱体,真也麻烦,肺部大约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还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
大约这里的环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闻不问,也是使病缠绵之道。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同日日记:“夜始于淡[痰]中见血。
”病情更严重了。
八月十六日,鲁迅致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
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
杨君夫妇之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
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急中开口。
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
但成绩恐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

倘在中国,实很难想出适当之处。
莫干山近便,但我以为逼促一点,不如海岸之开旷。
”则赴日本的念头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终没有明确说出一个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
”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
”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
”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
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
”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
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
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
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
”二十八日致杨霁云:“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
”先前还说“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现在取消计划,或与前一日日记所载“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不无关系,亦即鲁迅所说“再与医生一商”。
黄源《鲁迅先生》则云:“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
” 鲁迅此后几封信里,所说都是这个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亲:“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
”七日致曹靖华:“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
”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
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
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
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 以上就是鲁迅拟议赴日疗养,而最终未能成行的始末。
由此可知,周海婴转述周建人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说“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并非事实,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
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
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
”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
顺便说一下,其后鲁迅欲迁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释。
十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
”十二日,鲁迅致宋琳:“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
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
” 我讲这些,只想说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
有朋友说,“种种迹象表明,他内心已经预言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态。
”对此恕我稍有异议。
我觉得鲁迅大概预言不了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事,他赴日疗养的打算即可视为一个例证;当时局势非常复杂,不光鲁迅,就连包括当轴诸公在内的其他人同样也预言不了。
鲁迅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就在这年十月十九日辞世——仅仅二十一天前,他还在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的信中说:“我前一次的信,说要暂时转地疗养,但后来因为离不开医师,所以也没有离开上海,一直到现在。
现在是暑气已退,用不着转地,要等明年了。
”然而鲁迅已经没有明年了。
这是他笔下我读了最感辛酸和绝望的一节文字。
随机文章隋为什么才只短短三十七年?运30运输机最新消息曝光,或改用两喷气式发动机人们被现实打败的青蛙效应,温水煮青蛙竟然是假的(谣言)真的有人拍到了小精灵,英国妈妈在现实中看到花仙子神仙为什么要走南天门,天庭作为高维空间只有南天门一个通道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日轮花真的吃人吗,解密食人花吃人原因 花朵是黑寡妇帮凶
日轮花外表艳美,且芳香诱人,传闻这类花是毒蜘蛛的帮凶,协助其把人咬死。
日轮花真的吃人吗?下面我们解密食人花背后故事。
日轮花真的吃人吗当作一种食人花,日轮花有着非常灵敏快速的反应,还有着巨大的力气。
当有人在野外碰到它,不管是茎、叶、花等,都能把人抓住。
日轮花的叶子会变成鹰爪一样,抓住人不放,而此时潜藏在这个植物后面的黑寡妇蜘蛛会迅速爬到人的身上,咬人,因为这类蜘蛛毒素很强,会快速致人死亡,最后把人吃掉。
曾经有个科考队遇险日轮花的故事,话说这只考察队到亚马逊考察,其中有个新队员张晓林,对这里环境都很好奇。
某天张晓林在溪边洗完澡,正打算离开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
果然,在附近发现一株陌生植物,该植物拥有大叶片,大约一米的长度,几十个叶片围着主干形成轮状。
更让人惊奇的是,绿叶上生长着非常美丽的大花,香气十足。
张晓林看到这一幕,不由自主的向前触摸花朵。
而就在此时,惊恐的事情发生,周围的绿叶迅速将其缠住,使他不能动弹。
随之而动的,就是有大群的蜘蛛涌向并且啃咬他的身体,此时张晓林迅速拿出信号枪叫来了同伴,这才脱险。
蜀汉棋局中的弃子:解码刘封之死的三重政治密码
养子在的泪眼中自刎而亡,这位曾以武勇震慑东三郡的将领,最终沦为权力天平上的祭品。
其死亡背后交织着继承危机、战略失误与派系倾轧的三重绞索,折射出时代最残酷的政治法则。
一、继承危机:下的身份困局 刘封之死本质上是宗法制度与现实政治的剧烈碰撞。
作为刘备在荆州时期收养的义子,刘封早年因 武艺气力过人 备受器重,甚至一度被视为继承人培养。
但公元207年的出生彻底改写了权力格局——这位具有汉室血脉的嫡子,使刘封的 养子 身份成为致命缺陷。
陈寿在《》中直言其身处 嫌疑之地 ,这种身份尴尬在刘备称汉中王后愈发凸显。
刘备的应对策略充满政治算计:通过册立刘禅为太子、派遣刘封远征上庸,看似重用实则疏远。
但人事安排的失衡埋下隐患——让年仅二十余岁的刘封统领孟达等老将,既无法建立威望,又陷入权力真空。
当败亡、孟达叛逃时,刘封既无能力力挽狂澜,更无法平息蜀汉内部对 废太子 的猜忌。
这种身份困境,使其注定成为政权过渡期的牺牲品。
二、战略崩盘:东三郡失守的连锁反应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襄樊之战,成为刘封命运的转折点。
关羽兵败被杀、荆州丧失的直接导火索,正是刘封与孟达的 见死不救 。
但深层原因在于刘备的战略误判:将东三郡这枚连接荆益的战略棋子,交给缺乏政治智慧的刘封镇守。
该地区作为新附之地,内部兄弟等豪强势力暗流涌动,而刘封非但未能安抚,反而以 夺达鼓吹 的侮辱性行为激化矛盾。
孟达的叛逃更具标志性意义。
这位东州派代表人物率四千部曲降魏,不仅使上庸防守力量锐减,更在蜀汉内部引发连锁反应。
东州派作为仅次于荆州派的第二大势力,其核心成员的叛逃迫使刘备必须有人担责。
当曹魏、联军压境时,申仪的背叛彻底击垮防线,刘封的败逃使 跨有荆益 的战略构想化为泡影。
这种战略层面的崩盘,为刘备的清算提供了合法性外衣。
三、权力博弈:诸葛亮的隐秘推手 在刘封之死的决策链条中,诸葛亮扮演着关键推手角色。
其劝谏刘备 封刚猛,易世之后恐难制御 的言论,暴露出蜀汉权力结构的深层焦虑。
刘封作为刘备嫡系,不仅在军中享有 气力过人 的威望,更与孟达、申氏兄弟等地方势力存在复杂关联。
若刘备去世,年仅十三岁的刘禅根本无法驾驭这位 假子 ,蜀汉极可能重演诸子争位的悲剧。
诸葛亮的隐忧更在于权力制衡。
当时蜀汉内部存在三大势力: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派、以为代表的东州派、以及等本土将领。
刘封的存在将打破这种微妙平衡——其养子身份可能获得部分将领支持,而刚猛性格又易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通过清除刘封,诸葛亮既消除了潜在威胁,又强化了 尊刘禅、尊法度 的政治正确,为后续北伐扫清障碍。
四、历史镜像:权谋法则的残酷演绎 刘封之死绝非孤立事件,而是三国权力法则的典型注脚。
在袁绍废长立幼引发官渡惨败、确立门阀统治的对比中,刘备的选择展现出封建帝王的冷酷理性。
当刘封临刑前叹道 恨不用度之言 时,他或许已意识到:在权力漩涡中,个人武勇与战功终究难敌制度性安排。
这种悲剧性命运,在时期的 挥泪斩 、遇刺后的权力真空等事件中不断重演。
从现代政治学视角审视,刘封之死本质上是 预防性打击 的经典案例。
刘备集团通过牺牲边缘人物,既转移了荆州之败的舆论压力,又为新君登基铺平道路。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政权存续捆绑的权谋艺术,在后世王朝的 中反复上演。
当历史尘埃落定,刘封的悲剧早已超越个人层面,成为解读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切片。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