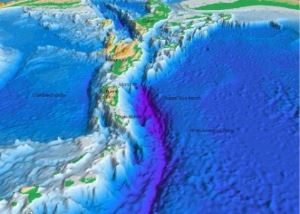在古时候中国的农民起义欧洲的有什么分别?又有什么相同点

“起义”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的词。
中国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从来没有“农民起义”连用。
比如,《》“汝水”条下,有“汝
【千问解读】
“起义”是一个有着明确的道德判断的词。

中国古典文献中有“起义”一词,但从来没有“农民起义”连用。
比如,《》“汝水”条下,有“汝南太守周矜起义于悬瓠者是矣”之句。
《志·传》裴注中,有“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之句。
《通典》中有“篡晋,宋武帝起义讨之”、“大唐高祖起义至京师”、“大唐起义太原”等句。
《》中,“高祖斩白蛇而起义”、“斩蛇起义”等句,出现频率也很高。
“农民起义”一词最早见于何人作品,很难搞明白。
可以肯定的是,要到50年代,该词才在报刊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出现(40年代后期的《新华日报》,已较频繁使用该词)。
在《38年前重要剪报资料库》中检索“农民起义”,仅能得到得1项结果(检索“起义”有130项结果)。
孙中山生平文章,经常使用“起义”一词,但在“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农民起义”,结果也是0(检索“起义”有481笔资料)。
不止是报刊和政治人物,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也很少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4年开明书店“中学生丛书”出版《晚明流寇》(王耘庄著)一书,专供初中学生各科课外阅读之用。
该书总结农民暴动产生的六大原因——1、天灾流行;2、赋税繁苛;3、政治腐败;4、外患频仍;5、兵变迭起;6、乡官虐民——可谓对农民充满了同情,但作者仍以 “盗贼之祸”名之,未使用“农民起义”一词。
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蔡雪村著)、1935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薛农山著)等,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而多用“暴动”、“流寇之乱”、“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农民骚动”等词。
蔡雪村是留苏地下党、薛农山曾加入陈独秀组织的“无产者社”,属于左翼学者。
钱穆、吕思勉这些非左翼学者的著作里,也没有“农民起义”之说。
图:上世纪50年代,“农民起义”一词开始井喷,图为1954年出版的《中国农民起义论集》封面及前言。
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这是民国史家对农民怀有深厚的同情,却又很少使用“农民起义”这个词的主要原因。
钱穆的解释很有代表性: “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秦末刘、项之乱,可谓例外。
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
近人治史,颇推洪、杨。
夫洪、杨为近世中国民族革命之先锋,然此固然矣。
然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成就何在?建设何在?此中国史上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常不为民族文化进展之一好例也。
”(《〈国史大纲〉引论》) 也就是说,动机层面的正义,不足以抵消手段和结果层面的非正义。
比如,李秀成谈起事初期裹挟民众的诀窍,乃是“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

寒家无食,故而从他。
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为防掳来之兵丁逃逸,严格控制士兵私财,甚至在士兵脸上刺字“”,以断其归路。
这样的手段,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正义。
太平军素有“打先锋”之惯例,“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
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
”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经太平天国之役后,至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
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的研究认为,1851~1864年,共约造成7330万的人口损失。
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义。
这些也是钱穆评价太平天国“其扩大依然是恐怖裹胁政策的效用”、感慨“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的缘故所在。
图:钱穆 简言之:“农民起义”是一个带有明确褒义色彩的词汇,并非所有的“民变”(我认为这是一个中性词),都可以被称作“农民起义”。
一场“民变”是否算“农民起义”,不但要考察其动机是否正义,还需要考量其手段和诉求是否正义。
从这个角度来打量中国历史,就不难发现,很多以往被理所当然视为“农民起义”的民变,其实只能算做“农民暴动”,动机(原因)是正义的,手段和结果则未必。
比如,《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视为下贱之人,涉及刑罚时动辄“黜为农”: “官或违犯十款天条及逆命令受贿弄弊者则为奸,由高贬至卑,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者,黜为农。
……凡滥保举人及滥奏贬人者,黜为农。
……但凡在尚保升奏贬在下,诬,则黜为农。
……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
” 这就已经与“农民起义”相去甚远了。
欧洲古代的“民变”情形,可参考《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下表述: “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人头税大幅增加。
该税开征于几年前。
人人都要缴纳。
起义农民从肯特和埃塞克斯涌向伦敦。
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1377--1399在位)和幕府没有及时采取军事行动。
起义军在泰勒(War Tyler)率领下攻入伦敦城,捣毁了萨伏伊宫(Savoy)。
该宫主人为兰开夏(Lancaster)公爵。
起义军在伦敦城郊向国王递交了请愿书。
国王似乎有意妥协,但起义军还是攻占了王廷要塞伦敦塔,并在城外的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再度与国王谈判。

泰勒当着国王的面漱口并要了一杯啤酒,被伦敦市长杀死。
国王夺回了伦敦,镇压了起义军。
从起义军向国王提出的要求,可以看出他们的真正诉求,也可以理解伦敦之外的大修道院为什么会成为农民的攻击目标。
起义军的主要要求如下:废除农奴制(仍存在于英格兰东南部),废除黑死病之后制定的限薪劳工法,百权参与乡村政务,消灭英格兰教会的世俗财产。
最后一点并不算激进,当时威克里夫(John Wyclif)的教会改革思想已经广为流传,甚至得到了兰开夏公爵的支持。
“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在德意志南部和中部爆发(包括现今奥地利和瑞士部分地区)。
该地区的很多农民都属于农奴,早已不堪重负,而伯爵、修道院长和骑士等小领主却日渐增多。
这些小领主名义上归德意志国王()管辖,却享有自治权,通常占据几个村落,既当大地主,又作领主。
这种双重身份引起了农民的反抗。
德意志南部的农民不仅发起暴动,还展开了宣传攻势,为自己辩护。
起义源头在士瓦本北部,起义者用简洁的语言归纳了自己的主张,并作为宣言四处印发。
《梅明根十二条》(Twelve Articles of Memmingen)就是一个范例,明确提出:农民有权选举乡村牧师,废除农奴税,削减什一税,农民自主决定公共林地、牧场和水源的使用,要求地方法庭尊重当地习俗,不采用领主们强加的夹杂着罗马法的法规。
”(维姆·布洛克曼 彼得·霍彭布劳沃/著,《中世纪欧洲史》,花城出版社,2012,P277-278。
) 如果《中世纪欧洲史》的以上描述没有错误,那么,“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和“1525年德意志农民起义”,确实与“农民起义”的概念比较契合,他们的动机(不堪重负)、手段(对抗压迫者和剥削者)和诉求(基于自身利益),均具备正义性。
廓清了“农民起义”的概念,文章开篇的问题,其实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的民变有什么区别? 区别如下: 中世纪的欧洲,是一种“领主分封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领主的暴政,他们也比较容易找到领主,进行直接对话。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大一统的郡县制。
民变者所反抗的,是皇权直接制定或者间接衍生的暴政,但他们很难直接与皇权对话,往往只能和皇权的代理人打交道。
前者可以直接与领主对话,或展开谈判,或暴力对垒。
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往往距离“农民起义”往往较近。
后者直接面对的是皇权的代理人(要么是郡县的武装力量,要么是中央的武装力量),为自身利益计,小规模的“民变”,往往更乐于落草为寇去侵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郡县的武装力量对抗,比如民国年间,河南因军阀混战“民变”迭起,基本上走就是盗匪路线;大规模的“民变”,也往往更乐于去“掳掠州县”,伤害更弱势的普通民众,而非直接与中央的武装力量对抗,赤眉、绿林、黄巾、黄巢、李自成,这些民变者,都曾辗转过小半个或大半个中国。
如此,民变在手段与结果层面,也就与“农民起义”越来越远。
这种区别,与“民族性”、“国民性”、“文化基因”之类的概念毫无关系,只是不同现实环境下的不同的“理性选择”。
郡县制下,地方郡县官僚只是皇权的代理人,郡县不是他们的私产,他们犯不着往死了镇压从其他地方流窜过来的民变者;民变者也很清楚,掳掠其他郡县的普通百姓,风险要远远低于直接和国家机器(郡县军队、中央军队)对抗。
领主制下,封地是领主的私产,有强烈的的抵御外来民变者的动力,民变者们也清楚,去掳掠其他领主治下的百姓,风险不一定低于直接反抗自己的领主。
这也是领主分封制下,很少出现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的全国性民变的原因。
随机文章中国万里长城有多长?21196公里(俄罗斯东西跨度2倍)揭秘黑天鹅和白天鹅的区别,黑天鹅轻易换配偶/白天鹅至死不渝详解北极和南极的区别,南极最低温度零下90度比北极更冷土耳其SOM巡航导弹,可在防空系统外精确打击目标二战钢铁火神之喷火坦克,苏联红军火烤日本关东军(威慑杀敌利器)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闽越国故地今何在:从东南边陲到现代福建的千年嬗变
核心区域覆盖今福建全境,北接浙江南部(温州、台州等地),南抵广东潮汕、梅州地区,西连江西铅山,东濒东海。
发现表明,闽越国都城东冶(今福州冶山一带)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当时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其王城遗址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面积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二。
这一疆域的形成与越国遗民的迁徙密切相关。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战败被杀后,部分越人从浙江绍兴一带航海入闽,与福建原住民“七闽”部落融合,形成新的族群——闽越人。
他们不仅在福建北部建立政权,还通过海路向潮汕、梅州等地拓展,使闽越文化的影响力辐射至整个岭南东部。
历史沿革:从方国到郡县的制度变迁 闽越国的政治命运始终与中原王朝的扩张紧密相连。
建国初期(前334年—前221年):越国遗民在福建建立独立政权,采用世袭君主制,与中原诸侯国形成对峙。
秦代统治(前221年—前202年):后,在闽越故地设闽中郡,但仅废除无诸的王号,改封“君长”,实际仍由闽越贵族统治。
这种“郡县其表,方国其里”的特殊制度,为后世闽越国复国埋下伏笔。
西汉复兴(前202年—前110年):战争中,无诸率军助击败,获封闽越王,重建王国。
汉初“”的政策使闽越国迎来鼎盛期,冶铁、造船、纺织业高度发达,铁制农具与兵器普及,甚至出现“带甲百万”的军事力量记载。
最终覆灭(前110年):因闽越王余善刻“武帝”玺自立为帝,调遣四路大军围攻,最终将闽越王族及民众迁往江淮地区,彻底终结其地权。
考古实证:武夷山下尘封的王城记忆 闽越国的物质文明在武夷山南麓的城村遗址中得到完整呈现。
这座始建于公元前202年的王城,以河为壕堑、以山为屏障,采用“半悬空”建筑技术防潮防虫。
考古发掘出土的2.02米空心砖、15公斤铁犁、81.5厘米铁矛头等文物,证明其冶铁技术已达同时代中原水平。
王城内的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布局严谨,出土的“万岁瓦当”与五齿耙更彰显其皇家气派与农耕文明成就。
遗址中的宫中浴池排水系统至今仍清晰可见,王宫古井的泉水历经两千余年仍清冽甘甜。
这些遗迹与风格宫殿基址共同构成“中国的庞贝古城”,为研究东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提供实物证据。
文化传承:从图腾崇拜到闽南文化的基因 闽越国的文化印记深刻影响着后世福建地域文明。
其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在《说文解字》中记载为“东南越蛇种”,至今仍可从闽南地区节赛龙舟的“龙首蛇身”造型中窥见一斑。
语言方面,闽南话与潮汕话的高度相似性,印证了闽越国时期潮汕属其疆域的历载。
经济领域,闽越国推广的铁器与曲辕犁技术,为福建后来成为“海上”起点奠定物质基础。
手工业方面,专供王侯享用的荃葛等纺织品,预示着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纺织业繁荣的先声。
而闽越人“善舟楫”的传统,更直接催生了福建造船业与海洋贸易的千年辉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闽越国故地今何在:从东南边陲到现代福建的千年嬗变
核心区域覆盖今福建全境,北接浙江南部(温州、台州等地),南抵广东潮汕、梅州地区,西连江西铅山,东濒东海。
发现表明,闽越国都城东冶(今福州冶山一带)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是当时东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其王城遗址南北长860米、东西宽550米,面积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二。
这一疆域的形成与越国遗民的迁徙密切相关。
公元前334年,越王无疆战败被杀后,部分越人从浙江绍兴一带航海入闽,与福建原住民“七闽”部落融合,形成新的族群——闽越人。
他们不仅在福建北部建立政权,还通过海路向潮汕、梅州等地拓展,使闽越文化的影响力辐射至整个岭南东部。
历史沿革:从方国到郡县的制度变迁 闽越国的政治命运始终与中原王朝的扩张紧密相连。
建国初期(前334年—前221年):越国遗民在福建建立独立政权,采用世袭君主制,与中原诸侯国形成对峙。
秦代统治(前221年—前202年):后,在闽越故地设闽中郡,但仅废除无诸的王号,改封“君长”,实际仍由闽越贵族统治。
这种“郡县其表,方国其里”的特殊制度,为后世闽越国复国埋下伏笔。
西汉复兴(前202年—前110年):战争中,无诸率军助击败,获封闽越王,重建王国。
汉初“”的政策使闽越国迎来鼎盛期,冶铁、造船、纺织业高度发达,铁制农具与兵器普及,甚至出现“带甲百万”的军事力量记载。
最终覆灭(前110年):因闽越王余善刻“武帝”玺自立为帝,调遣四路大军围攻,最终将闽越王族及民众迁往江淮地区,彻底终结其地权。
考古实证:武夷山下尘封的王城记忆 闽越国的物质文明在武夷山南麓的城村遗址中得到完整呈现。
这座始建于公元前202年的王城,以河为壕堑、以山为屏障,采用“半悬空”建筑技术防潮防虫。
考古发掘出土的2.02米空心砖、15公斤铁犁、81.5厘米铁矛头等文物,证明其冶铁技术已达同时代中原水平。
王城内的宫殿区、作坊区、墓葬区布局严谨,出土的“万岁瓦当”与五齿耙更彰显其皇家气派与农耕文明成就。
遗址中的宫中浴池排水系统至今仍清晰可见,王宫古井的泉水历经两千余年仍清冽甘甜。
这些遗迹与风格宫殿基址共同构成“中国的庞贝古城”,为研究东南地区早期国家形态提供实物证据。
文化传承:从图腾崇拜到闽南文化的基因 闽越国的文化印记深刻影响着后世福建地域文明。
其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在《说文解字》中记载为“东南越蛇种”,至今仍可从闽南地区节赛龙舟的“龙首蛇身”造型中窥见一斑。
语言方面,闽南话与潮汕话的高度相似性,印证了闽越国时期潮汕属其疆域的历载。
经济领域,闽越国推广的铁器与曲辕犁技术,为福建后来成为“海上”起点奠定物质基础。
手工业方面,专供王侯享用的荃葛等纺织品,预示着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纺织业繁荣的先声。
而闽越人“善舟楫”的传统,更直接催生了福建造船业与海洋贸易的千年辉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