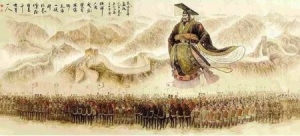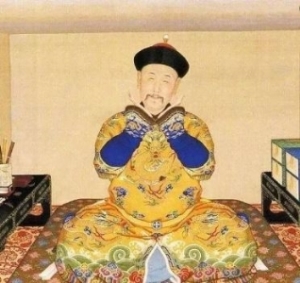克里米亚战争:为意大利的统一制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意大利”(Ita
【千问解读】
“意大利”(Italia)一词来源于时代,在当时,今天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利亚地区被人们称为“威大利亚”(Vitalia),意为“小牛犊成长的乐园”。

后来这个词的词头字母“V”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省略,于是就形成了“Italia”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意大利亚”。
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新兴的罗马共和国用“意大利”为整个亚平宁半岛命名,自此,“意大利”逐渐成为世人所熟知的地理概念。
由于教会权力过于强大(罗马是教廷的所在地),意大利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世俗权力核心,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意大利本土走向统一的历程。
另外,因为意大利位于“”,经常成为欧陆各派强权争夺角逐的战场,这使得意大利缺乏实现统一的外在环境,从而也在客观上造就了意大利的分裂局面。
在内外原因的共同作用之下,意大利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处在的“碎片化”状态之中。
18世纪以来,随着蒙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别是战争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涤荡与冲击,意大利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广泛苏醒,追求统一与富强成为意大利人共同的民族诉求和心灵期盼。
但彼时意大利的统一之路可谓困难重重、遥遥无期。
一方面,意大利境内邦国林立,教权强大;另一方面,法国和奥地利这两大强邻都对分裂的意大利、垂涎欲滴。
但这种看似无解的困局却因千里之外的一场国际战争而打开了局面,这场战争就是英、法、土与沙俄之间的,它为意大利的统一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外部环境机遇。
1853年,为争夺多瑙河下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控制权,土耳其与沙皇俄国之间爆发了战争。
开战初期,由于双方在军事实力上存在着差距,处于弱势的土耳其一方在交战中连战连败,特别是在锡诺普之战中,土耳其海军遭到了沙俄黑海舰队的毁灭性打击。
眼见土耳其旦夕难保,英、法两国出于遏制沙俄势力扩张的共同目的,决定联手加入战团。
1854年初,沙俄与英、式彼此宣战,至此,沙俄与土耳其之间的区域性战争正式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
由于交战双方争夺的主要是沙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军港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这场也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
由于塞瓦斯托波尔城高垒坚,加之守军作战极为顽强,英、法联军一时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战争随之陷入僵持状态。
为了早日打破僵局,同时也为了扩大己方阵营的实力,法国在征得英国同意之后,派出特使赴都灵,力劝撒丁王国(当时意大利最强大的邦国)参战。
撒丁首相加富尔认识到,参加此战将给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带来重大的外交机遇,遂决定正式参与到英、法、土耳其一方共同对沙俄作战。
1855年1月26日,15000名撒丁军人从国内出发,奔赴克里米亚前线参加对俄军事行动。
较之于其他参战国,身为蕞尔小邦的撒丁王国虽然出兵甚少,但却通过此战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与英、法这两个欧洲大国的邦交。
1855年9月,英、法、土耳其、撒丁联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攻占了塞瓦斯托波尔,至此沙俄的失败已成定局。

在此之后,交战双方间的战事渐趋平息,各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外交战场上的争斗中。
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统一意大利的邦国,撒丁王国在战后和会上的诉求是孤立宿敌奥地利,并争取其他大国对意大利统一的同情和支持。
由于判断失误和认知偏差,加富尔在战时和战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奉行“营垒外交”路线,即将欧洲各主要大国划分为“自由阵营”和“专制阵营”两个泾渭分明的集团:前者主要由英、法组成;后者则由俄、奥组成。
根据这一判断,既然意大利统一的最主要障碍来自于“专制阵营”的奥地利,那么撒丁王国就应该依托“自由阵营”的英、法两国支持,达成将奥地利的势力从意大利驱逐出去的目标。
在加富尔看来,奥、俄两国都属于“专制阵营”,如能重创沙俄,则奥地利必然会在俄国动荡的波及下而受到影响,为意大利的统一除去一大劲敌。
这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定输赢的想法,虽然在今天看来显得颇为幼稚,但在当时却是加富尔外交理念的重要立足点。
因此,当英国鼓吹在攻取塞瓦斯托波尔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俄境作战时,加富尔立即表现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大有一副紧随英、法同沙俄打到底的架势。
但是无情的现实很快便粉碎了他的迷梦。
由于深入俄国境内作战需要法国陆军的参与,而英国又拒绝了法国在北意大利扩张势力的要求,于是英法两国之间产生了裂痕。
战败的沙俄见到英法之间出现嫌隙,马上见缝插针,先是同法国进行秘密外交接触,以求进一步离间英、法,随后又做出了向盟国正式求和的决定,以求在未来的和会中通过与法国的合作将战争损失降到最低。
加富尔起初曾不相信“自由阵营”与“专制阵营”之间会达成妥协,并通过外交渠道力劝法国继续参加对俄战争。
但形势比人强,由于各主要参战国均表示愿意参加停战谈判,因此战争已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
1856年2月1日,克里米亚战争的各主要交战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签署议定书,并决定于2月25日在巴黎召开战后和平会议。
这样一来,由于加富尔先前一直在鼓吹继续进行对俄战争,撒丁王国在战后外交中一度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之中。
不过加富尔毕竟是一位机智精明的政治家,看到基于“意识形态”的“营垒外交”破产之后,他马上决定改弦更张,同欧洲列强展开新一轮的外交博弈。
由于害怕沙俄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强势扩张损害自身利益,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积极反俄,从而使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俄奥同盟关系彻底破裂。
在战后举行的巴黎和平会议中,沙俄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反击奥地利背盟行为的目的,遂采取了拉拢法国,适度满足英国要求,同时坚决打击奥地利的外交举措。
在这个过程中,撒丁王国也成为了沙俄的拉拢目标,因为沙俄可以通过支持撒丁王国来削弱奥地利的势力。
与此同时,为了将奥地利的势力从北意大利驱逐出去,法国也采取了亲近撒丁王国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在与奥地利争夺北意大利控制权的斗争中,撒丁王国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伙伴。
另外,通过在波兰和意大利问题上的利益交换,俄、法两国在和会中进一步达成了默契,这就为接下来撒丁王国与俄、法间的新合作铺平了道路。
1856年2月26日,加富尔与沙俄外交代表奥加洛夫进行了首轮磋商,后者在加富尔面前对奥地利进行了激烈抨击,并为过去因照顾奥地利而未与撒丁王国建交深表悔恨。

这次会谈使加富尔收获良多,此后撒丁王国与沙俄的关系迅速升温,1856年夏,撒丁与沙俄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奥地利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撒丁与法国的关系也在加富尔的运筹下得到了快速发展。
1856年4月8日,加富尔在巴黎和平会议上针对奥地利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和会主席、法国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不仅对加富尔的讲话持默许态度,并且还将这篇讲话列入了会议记录之中。
该举动表明,此时的法国已对撒丁王国的反奥诉求采取了公开支持的态度。
当然,在与法、俄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同时,加富尔也十分渴望拉近与传统友邦英国的关系。
但由于对法、俄接近持警惕态度,英国决定站在奥地利一边,以防止法、俄接近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
因此英国不希望撒丁王国驱逐奥地利的在意势力,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甚至规劝加富尔改善与奥地利的邦交关系。
英国的亲奥态度让加富尔感到既无奈又失望,他在给撒丁王国驻英大使的信中指出:“英国背弃了自由主义的事业,成了奥地利私欲的工具。
”虽然如此,在先前“营垒外交”的挫折中日渐成熟起来的加富尔并未采取与英国为敌的政策,他依旧与英国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以求英国能在未来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冲突时保持中立。
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加富尔的这一努力基本达到了目的。
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中期改变欧洲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为意大利实现国家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助力。
在这场战争中,最有实力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将法、俄争取到了反奥阵营之中,从而使奥地利这个意大利统一之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处在空前孤立的状态之中,这就为日后撒丁王国统一整个意大利创造了良好的开局。
此后,在1859年的反奥战争中,撒丁与法国联军力挫奥地利军队,撒丁王国乘胜收复了除威尼斯以外的北意大利地区。
1860年,意大利传奇英雄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南下攻灭了两西西里王国,随后南意大利地区也并入撒丁王国。
撒丁王国随即于1861年正式改名为意大利王国。
1866年,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利用普鲁士击败奥地利的机会,收复了威尼斯。
1870年,意大利又利用法国被普鲁士打败的机会拿下了罗马,教皇被迫退居梵蒂冈。
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自此正式形成。
今天再来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虽与意大利毫不相干,但却在不经意间为意大利的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这或许也可以被看作是“蝴蝶效应”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吧。
随机文章世界上最巨大最清晰ufo曝光,头顶几百米高空飞过发怪声揭秘赤练蛇有毒吗,长有后沟毒牙(被咬有一定几率中毒昏迷)揭秘牛顿神学发现了什么,追根溯源宇宙还是由上帝手中诞生的(NO)山神和土地的区别,山神身材魁梧/土地年老色衰(一个修仙一个修神)路飞第几集吃光明果实,网络谣言/路飞靠橡胶果实通关(被掏空)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核战争来临该怎么办?中国哪些地区最容易被打击
最安全的地方不是防御导弹最多的地方,而是敌人不敢打的地方,防御导弹越多反而说明这个地方越容易遭到攻击。
目前世界上敢与中国发生核战的国家几乎没有,所以本文讨论的也是基于常规战争的假设,那么常规战争中,地方最怕的是什么?怕你使用核武呗!中国不是说不首先使用核武吗?确实,但是别忘了,中国还有后面的一句补充,当中国的核设施和对民生极为主要的设施遭到攻击时,中国将对此看成对实施的核打击,中国将予以核还击。
两国交战,除非是有血海深仇,否则出于人道主义不会攻击民生相关的重大设施。
一个常规的重大民生设施的保护范围本来极其有限,但是核设施就不同了。
中国的核电站可能是最危险的地方核设施由于其特殊性,一旦遭到重大的攻击,会影响一座城市,所以在战前、战时,敌方一定会精确定位中国的核设施,幸免在其城市以及相邻城市间袭击,尤其是核电站,占地面积大,虽明显,实为更加安全,怕就怕你看不到。
从1964年到1972年,我国科学家曾对4座模拟大坝进行了7次核武器轰炸实验,取得了极其珍贵的数据。
实验显示的最严重情况是,当大坝被100万吨当量的核武器命中时,会产生1000米溃口。
从1978年到1988年,专家又连续进行了三峡溃坝实验,研究大坝在遭受核武器袭击后,溃坝洪水的影响范围,以及减少损失的对策。
文件显示,如果当时冷战 升高,美国将对苏联、苏联的卫星国以及联盟的1200个目标展开毁灭性的原子弹攻击,中国无论参战与否,人口密集的城市也将被原子弹攻击,利用放射性物质 将平民杀死。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将人口密集地方的平民列为灭绝目标。
中国的城市目标包括北京在内,多达23个。
如果大国战争的话应该没有胜利者,核子武器可以把人类彻底从地球上抹去啊.
玫瑰战争余晖下的治理重构:约克王朝如何重塑英格兰国家机器
这个仅存续24年的王朝虽未彻底终结封建割据,却通过行政改革、财政整顿与司法重塑,为的中央集权奠定了关键基石。
一、王权重构:从到垂直统治 约克王朝的统治者通过军事胜利与政治联姻,逐步瓦解了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
爱德华四世即位后,立即废除的 郡守 ,改由国王直接任命治安法官。
这些由骑士、乡绅组成的基层官员,需定期向财政署汇报税收与司法情况,形成 国王-治安法官-社区 的垂直管理体系。
在约克郡,治安法官每年需核查辖区内12个百户区的治安巡逻记录,其薪资与考核均与国王满意度挂钩,这种制度设计有效遏制了地方豪强对司法的干预。
王朝开创的 王室特派员 制度更具突破性。
1471年,爱德华四世向北方六郡派遣由中央财政署直接供养的特派员,负责监督羊毛贸易税征收。
这些官员手持盖有国王火漆印的账册,可随时抽查商人的交易记录,使约克郡的羊毛出口关税收入在三年内增长40%。
这种 钦差大臣 式的监督机制,标志着英格兰王权首次突破封建分封制的地理桎梏。
二、财政革新:国家机器的供血系统 约克王朝的财政改革堪称中世纪英格兰的 供给侧革命 。
针对兰开斯特王朝时期羊毛关税被贵族私吞的顽疾,爱德华四世在1475年颁布《关税统一法令》,将羊毛出口税由每袋3先令6便士提升至6先令,并规定所有税款必须通过伦敦皇家金库缴纳。
为规避地方贵族的盘剥,法令特别授权商人冒险家公司组建武装商队,直接将税款护送至首都。
这种 中央直收 模式使王室年收入从战争前的3万英镑激增至12万英镑,相当于当时法国王室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债务重组策略。
面对兰开斯特王朝遗留的18万英镑国债,王朝采取 债转股 方案:允许伦敦金融家以25%的折扣认购国债,换取未来五年王室呢绒采购的优先权。
这种现代金融手段的雏形,不仅化解了财政危机,更催生出英格兰首批职业金融家群体。
1480年伦敦金融区的地契记录显示,73%的新建商住楼宇由国债认购者建造,彰显改革对城市经济的刺激效应。
三、司法革新:王权至上的法律重构 约克王朝的司法改革堪称英国普通法发展的分水岭。
爱德华四世在1468年设立 北方巡回法庭 ,由三名王室法官组成流动审判团,每年在约克、达勒姆、兰开斯特三地巡回审判。
该法庭突破封建领主法庭的地域限制,可对涉及金额超过100英镑的案件行使终审权。
在1473年的 里彭羊毛商案 中,巡回法庭推翻了约克大主教法庭的判决,追回被侵吞的2000英镑关税,此案确立了 王室司法优先 原则,使北方郡的诉讼案件数量在五年内增长三倍。
王朝对法律文本的编纂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1474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朗兰牵头编纂的《爱德华法典》颁布,这是首部以国王名义颁布的成文法典。
该法典将封建习惯法与教会法中有利于王权的条款整合,如明确规定 未经国王特许,任何领主不得设立私人法庭 。
这种法律体系重构,使英格兰司法从 领主正义 向 国家正义 转型,为都铎王朝的《大宪章》修正案提供了文本基础。
四、治理遗产:被低估的制度创新 约克王朝的治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回响。
其建立的治安法官制度,经都铎王朝完善后成为英国地方行政的核心支柱,直至19世纪仍承担着征税、治安、济贫等职能。
财政署的 中央直收 模式,为伊丽莎白时代的关税制度改革提供了范本,使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司法领域的巡回法庭制度,经亨利七世改良后催生出 星室法庭 ,成为打击贵族叛乱的重要工具。
这个王朝最深刻的示在于:在封建制度尚未瓦解的时代,约克统治者通过制度创新而非暴力征服,实现了王权与地方势力的动态平衡。
当1485年理查三世战死博斯沃思原野时,其留下的不是满目疮痍的国土,而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机器。
这种 在传统框架内实现现代化 的治理智慧,或许比其军事胜利更具历史价值。
正如《英国宪政史》所言: 约克王朝的短暂统治,恰似中世纪英格兰向近家转型的渡桥,其制度遗产至今仍在英国司法档案中闪烁微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