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为什么会用"情色"诱惑太子宋孝宗?

后世的史料中有
【千问解读】
后世的史料中有关宋孝宗赵昚的记载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他通过宋高宗的考验坐上皇位的传奇经历。

他之所以能以非亲子身份继承宋高宗的皇位,一方面与高宗无子被迫在宗亲中选太子有关。
另外一方面,恐怕也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得益于他在一次处理宋高宗送给他十个美女问题上的出色表现。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难以置信,赵昚继承皇位与处理十个美女之间怎么会存有如此大的关联呢? 故事还得从1129年说起,就在这一年,金左副元帅宗维攻陷徐州,驱军南下,扼守在淮阳的军一战即溃,败走盐城,金兵,一路杀到扬州附近的天长军。
以往金军入侵时都是靠着韩世忠和岳飞等一批名将的顽强抗击,宋朝皇室才得保无忧。
但这次连韩世忠的军队都在与金兵交战中失败,自然使得宋皇室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屏障。
韩世忠的这次失败使宋高宗惊恐万分,逃跑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狼狈。
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在这次事件之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他唯一的儿子也在苗刘之变后死去。
加上太宗系的后人,在之变后基本被金国一网打尽,因此从太宗的后代之中几乎找不出可以继承皇位的合适人选。
为了不至于使自己在皇位落于外姓人氏之手,宋高宗被迫在的哥哥宋太祖的后代中寻找可以继承自己皇位的人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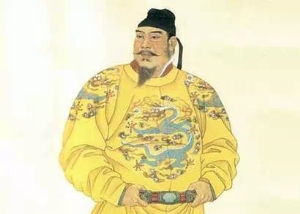
与宋太宗的后代不同,当时宋太祖的后代有上千人之多,可宋高宗想在这么多人之中选出合适的人选亦并非易事。
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宋高宗终于找到了一胖一瘦两个小孩。
在这两个太子人选当中,赵昚便是其中那个偏瘦的小孩。
刚开始,宋高宗对赵昚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而是比较中意胖点的小孩。
按理说赵昚继承皇位的机会应当也就到此画上了句号,但是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正在他放弃做皇帝的梦想之时,发生了一件微小的事情,进而使整个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次,宋高宗将赵昚和胖小孩叫到一起,恰巧此时闯进了一只猫,赵昚正地听宋高宗讲话,猫闯进来后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而胖小孩却不同,猫闯进来后他显得很惊慌,再也无心听宋高宗讲话,连忙伸脚去踢猫,动作极其粗鲁。
胖小孩这一粗鲁的举动彻底葬送了高宗原本对他的好感,最终,高宗打发走了胖小孩,将赵昚留在了宫中。
按理说,赵昚被留在宫中之后,皇位继承人非他莫属了,但是他在宫中待了将近有20年,却没有被确立为太子,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赵昚非宋高宗亲生,宋高宗始终对他怀有一定成见,希望多给自己留些时间,渴望出现能生育的奇迹。

其二是宋高宗的母亲韦不喜欢赵昚,而喜欢另一个养育在宫中的赵琢,她一直劝高宗立赵琢为太子,这使宋高宗在立太子的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不知如何取舍。
最终,他想出了一个既可以不使韦太后生气,又可以考验赵昚和赵琢的:给他们两人分别送去十名绝色处女,待半个月之后再将这些绝色佳丽召回来认真查验,谁破处最少,谁将是皇位的最佳人选。
宋高宗想出的这个招数很管用,效果也很明显。
送给赵昚的十个佳丽被召回来之后完好如初,而送给赵琢的十个佳丽却全部都不再是处女。
最终,赵昚通过了宋高宗的考验,顺利地被立为太子,直至登上皇帝的宝座。
后人评价宋高宗赵构,说他一生行事之中,唯有选太子是最称公允的,能上慰天地,下慰祖宗。
然而,一则有宋太祖的先例,二来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宋高宗选立孝宗,也实在是出于无奈了。
随机文章朱元璋23天不给他吃饭看到他傻眼:你怎么还活着中国万里长城有多长?21196公里(俄罗斯东西跨度2倍)黑林错觉怎么审判犯人,利用经验主义引导犯人说出实情探寻空中猛禽的虎头海雕捕猎技巧,白头海雕vs虎头海雕谁更厉害克苏鲁神话没有善神么,古神只是利用人类并非善意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永徽之后:唐高宗时代的权力更迭与治世余韵
从永徽六年(655年)册立为后到显庆四年(659年)集团覆灭,这段历史见证了皇权与相权的激烈博弈,也标志着唐代政治生态的深刻转变。
一、永徽余晖:背后的制度惯性 永徽之治(649-655年)的繁荣源于对贞观制度的延续。
即位之初,沿袭 三日一朝 改为 一日一朝 的勤政传统,修订《永徽律》并编纂《唐律疏议》,将法律条文与司法解释。
这种制度惯性使在人口、经济、军事领域持续突破:全国户数从贞观年间不足三百万户增至380万户,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抵里海、南达越南横山、北逾贝加尔湖,形成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的盛况。
但盛世表象下暗藏危机。
高宗虽延续政策,却在永徽四年(653年)设立常平署调控物价,暗示中央财政对地方经济的干预增强。
这种集权倾向与的政治特权形成矛盾,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二、显庆风云:皇权对相权的全面反制 永徽六年(655年)的 废王立武 事件成为权力格局转折点。
高宗在武则天支持下,突破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阻挠,改立武则天为后。
此举不仅是后宫争宠的结局,更是皇权对相权的宣战——当褚遂良以 的极式谏阻时,李治已决心打破 贞观遗风 下文官集团对皇权的掣肘。
显庆四年(659年)的 长孙无忌案 将这场博弈推向高潮。
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未予审讯即将其流放黔州,旋即赐死。
这场清洗不仅铲除关陇集团核心,更通过修订《姓氏录》打破自以来的,使 五姓七望 等世家大族失去政治特权。
武则天之兄武元庆、武元爽借此机会跻身政坛,标志势力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三、龙朔改制:中枢权力的结构性重组 权力清洗后,高宗启动 龙朔改制 (661-663年),对中枢机构进行根本性调整:废除二十四司,改设六官(司礼、司戎、司农、司徒、司空、司寇),试图构建皇权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同时提升地位,使文人学士获得参与机要的机会。
这种改革虽因操作复杂而半途而废,却暴露出高宗打破制、建立绝对皇权的野心。
军事领域同样经历变革。
灭、平百济的战争中,高宗突破 将从中御 传统,赋予前线将领更大自主权。
这种转变既带来军事胜利,也导致地方军阀势力抬头,为埋下隐患。
四、麟德迷局:二圣临朝的权力平衡术 麟德元年(664年),高宗因风疾目眩,开始授权武则天 垂帘听政 。
这种 二圣临朝 模式实为权力制衡的产物:高宗通过扶持武则天对抗关陇旧臣,又借李勣等将领制衡后族势力。
当武则天试图染指军权时,高宗立即提拔等将领,并在乾封元年(666年)泰山中刻意突出自己 天命所归 的形象。
这种平衡术在文化领域亦有体现。
高宗支持译经事业,却拒绝为其撰序,转而由自己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他重修《》时,特意增加《天文志》等科技篇章,彰显 文治武功 并重的帝王形象。
五、历史回响:治世转型的深层逻辑 从永徽到显庆的权力更迭,本质是唐代政治文明从 贵族共和 向 君主专制 的转型。
高宗通过瓦解关陇集团打破门阀政治,却因过度集权导致宦官势力崛起;武则天借机掌权虽开创 ,却使皇位继承陷入混乱。
这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轨迹,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再度显现。
在制度层面,永徽年间修订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典范,其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的理念影响后世千年;显庆年间设立的医学专科、数学科考,则推动制度向专业化转型。
这些制度遗产证明,即便在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中华文明仍保持着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
当后世回望这段历史时,看到的不仅是高宗个人的权谋算计,更是一个文明在制度创新与权力集中间的艰难抉择。
永徽之治的余晖照亮了显庆年间的改革,而显庆年间的震荡又为的到来提供了镜鉴。
这种治乱循环的历史逻辑,恰似《周易》所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权力更迭与制度演进中,书写着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密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