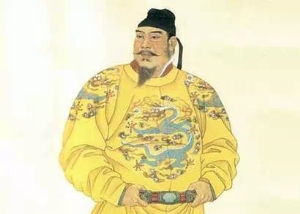战国历史上第一个连老天都敢射的亡国之君

众所熟知的、揠苗助长、野人献曝等,里面的二货主人公都是宋人。
除了普通老百姓,宋国的国君也常是被攻击的对象。
被一代领袖称之为“
【千问解读】
众所熟知的、揠苗助长、野人献曝等,里面的二货主人公都是宋人。

除了普通老百姓,宋国的国君也常是被攻击的对象。
被一代领袖称之为“蠢猪”的自不必多说,还有一位也是有名的招黑体质,他便是宋国的亡国之君——宋康王子偃。
史书记载,宋王偃穷兵黩武,好色淫乱,且又残暴不堪,大臣有进谏的动辄射杀,于是被其他诸侯称之为“宋”,痛恨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在宋王偃清一色的差评中,最为人诟病的还要数他的“射天”行为。
一、射天行为网络配图 什么是“射天”?《·宋世家》对此的记载是,“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
” 韦,指经过去毛等加工处理后的兽皮,即皮革。
县,通悬,悬挂之意。
所以,上面那句话的意思是,将用皮革做成的口袋盛满鲜血,高高地悬挂起来,然后用箭去射它,这种仪式便被称为射天。
对于宋王偃的这一行为,《春秋· 过理》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宋王筑为蘖台,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
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 ”。
鸱夷,据高诱注解,是一种较大的皮囊。
显然,宋王偃的行为是对天地的大不敬。
周人崇天敬天,周王更是自称为天子,因而,对于宋王偃的射天行为,周王的同姓及姻亲诸侯国极为反感,纷纷斥之为昏聩无道、罪大恶极。
后来的儒家对于宋王偃的评价,也大抵以负面为主。
不过,也有人持积极的评价,认为宋康王的“射天”,是对敬事鬼神传统的反叛,致力于打击鬼神迷信思想,是一种理性觉醒的体现。
据此说,宋康王实乃传统文化的革新者。
可惜的是,当时社会上鬼神观念还太过浓厚,不被时人所理解的宋康王,最终沦为了负面人物。
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上面两种看法,截然相对,谁对谁错?宋王偃为什么要做出“射天”这一壮举呢? 二、并非孤案 众所周知,宋是殷商的后裔。
周灭商后,封纣王的异母哥哥微子于商的旧都商丘,宋国就此建立。
从商人角度来看,宋王偃并不是第一个“射天”的国君。
《史记 ·殷本纪 》记载:“帝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

与之博,令人为行。
天神不胜,乃僇辱之。
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 `射天 ‘。
” 《史记 ·龟策列传 》记载:“(纣)杀人六畜,以韦为囊。
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强。
” 由上可知,武乙和纣王都曾经干过射天的事,再加上宋王偃,如此一来,殷人射天的行为,仅史书上有据可查的便有三次。
不难想象,实际发生过的恐怕会比这要多。
也就是说,“射天”并不是某个国君的单独行为,而有可能是商人一脉相承的某种习俗。
网络配图 因此,这一行为背后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它既不能以道德来衡量,更与进步或理性无关。
于是,上面的两种看法恐怕都非正解。
那么,“射天”这一行为背后的真实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三、宗教对立 商和周的关系,很多人都把它理解为一种线性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情形正如的那句名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不过,这种观念恐怕并不正确。
夏商周三代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平行并进式的互相发展,而没有前后相继的递进关联。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文化圈,商灭夏,周克商,其实是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
其情形更类似后来的元灭宋,而非秦汉魏晋之间的嬗代。
有关商、周间的不同,以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论述最为精妙、深刻。
在这篇大作中,王国维下了一个著名论断:“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这种观点后来存在不少争议,但大家的争议点更多在于,商周之变与周秦之变的剧烈程度高低,而对商周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观点却是大体认同的。
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在商周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宗教的差异是个显著特点。

而在宗教的差异上,至上神信仰的不同又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区别。
简单来说便是:商人信仰的至上神是“帝”,而周人则信仰“天”为最高神。
四、巫术诅咒 当我们明白“天”是周人而非商人的至上神时,再结合武乙射天的具体记载后,便可明白,“射天”实乃一种宗教行为。
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巫术行为。
天是周人的最高神,而天无形,于是商人用一个没有面目的皮囊来指代。
以箭射穿代表“天”的皮囊的行为,其实就是对周部落实施的一种黑巫术——通过打击周人的至上神,进而对周人产生伤害。
通过对商人三次射天巫术历史背景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明白这一点。
网络配图 武乙在位时,国力逐渐衰微,商朝东方的部族东夷逐渐强盛起来,他们分别迁移到淮河、泰山一带,其势力更是达到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
不仅东方,西部的各个部落也逐渐强盛,进而对商人产生威胁。
周人部落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此时的周人部落,是在位时期,季历是谁?他乃周文王的父亲。
周人部落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发展壮大,以至于到了文王时期,周人的势力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人势力的崛起,自然引起商人的担忧,因此,商人便有意对周人进行打压。
武乙举行的射天巫术便是其中的一种手段。
后来,为了遏制周人的崛起,武乙之后的文丁索性将季历囚禁了起来,一段时间后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处死了。
殷商末代国君纣王,采用射天巫术诅咒周人的背景自不用多说。
最后再说宋王偃。
宋王偃举行射天巫术的时机,发生在他东战齐、南战楚、西战魏等战争之后,所以,这一行为也是旨在通过对周人所信奉的最高神实施诅咒,以打击齐、魏等国,进而实现商人的伟大复兴。
本文为原创,未经官方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隋唐英雄侯君集简介 历史上侯君集是如何死的
侯君集自少年时代就勇武为人称颂,以有材且雄健著称,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是个胆大勇武的世家子弟。
在隋末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侯君集得识明主,投入了的幕府之中。
他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屡建功勋,被封为全椒县子,受到了李世民完全的信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爆发了,在这之前,侯君集出谋划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跟随李世民进入玄武门,诛杀了李世民的兄弟和李元吉。
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侯君集被封为潞国公,赐邑千户,升为右卫大将军,而此时的,食邑才有五百户,可见当时在李世民的眼里,侯君集比李靖重要的多。
侯君集讨伐吐谷浑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侯君集又升为兵部尚书,参议朝政。
贞观九年,他被任命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作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副手,讨伐吐谷浑。
五路大军直指吐谷浑,慕容伏允胆战心惊。
他放火烧荒,尽毁草原,然后躲进沙漠,给唐军来个坚壁清野。
侯君集主张穷追猛打,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李靖征讨吐谷浑国。
以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
部队到达鄯州,商议下一步军事行动。
侯君集说:“现在朝廷的军队已快到目的地。
而吐谷浑部队不去守住险要之地,实在是老天相助。
如果用精干的部队乘其不备,则有大胜可能。
等敌人逃到山谷里,攻克起来就难了。
” 李靖同意他的计策。
唐军兵分两路,李靖、薛万均往北路,侯君集、李道宗往南路,对慕容伏允展开了钳形攻势。
侯君集部穿越2000多里的不毛之地,人靠喝马血维持体能,马靠啃冰雪延续生命,终于在乌海(今青海苦海)追上了吐谷浑军,杀得吐谷浑人鬼哭狼嚎。
唐军翻越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在今天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全歼慕容伏允的吐谷浑军,慕容伏允走投无路,自缢身亡。
慕容伏允的儿子慕容顺也被唐军俘获,吐谷浑举国投降,唐军大获全胜,自此吐谷浑一举平定。
侯君集平定高昌国 贞观十一年,侯君集被封为陈州刺史,改封为陈国公。
明年,又拜为吏部尚书,进位光禄大夫。
侯君集以前根本不爱读书,进了李世民的 秦王府后才拿起书本补习功课,他天资聪颖,竟然很快小有成就,典选官员,制定考课,做得有条不紊,颇受时人赞美,出将入相,文武双全,正是大唐帝国官员的典型特征。
他一直走得很顺,少有挫折,心高气傲,耻居人下,就成了他一贯的心态。
连一向待人谦和的李道宗都看不惯他,认为他不是善类,早晚必为反贼。
侯君集如此狂傲,当然有他狂傲的资本,那就是他独担重任、平灭高昌国的赫赫战功。
高昌国是个与今天的伊拉克差不多大小的国家,位于中亚地区的咽喉地带,东面是强大的唐王朝,西面是西突阙这样凶悍的游牧民族,在强国的虎视眈眈之下,高昌国就有了墙头草的特征,在大国的缝隙之中谋求生存,于是,高昌国摇摆不定的举动就被大唐帝国视为对国家威严的挑衅。
高昌国王鞠文泰本来对大唐颇为恭敬,经常贡献一些奇珍异宝,贞观四年,鞠文泰亲自入朝晋见唐太宗,得到了丰厚的赏赐,鞠文泰的妻子还被册封为常乐公主。
来回的路上,见到大唐的西部地区因久经战争而城邑空虚、人民稀少,心里涌起了轻视的念头,于是悍然与西突厥勾结在一起,做出了几件让人侧目的事情。
他扣押了不少路经高昌的西域商人和贡使,不许他们前往大唐。
又和西突厥联合出击,攻打唐朝的西域属国伊吾和焉耆,连下焉耆数城。
焉耆王派使者向大唐求救,唐太宗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薛万均、契苾何力等将领直奔高昌而去。
高昌国王麴文泰听到这个消息,笑道:“唐国离我国七千里地。
荒漠,盐碱地有二千里。
既无水草,而且冬天风吹裂肌肤,夏天风吹如火烧。
行族商人一百人不能有一人到达。
岂能大军攻到这里?即使能够到达,在城外一两十天就会因吃完粮食而溃败。
我将趁机俘虏他们。
” 侯君集刚渡过荒漠,到达高昌地界。
就听到麴文泰死去,其麴智盛刚继位。
而且高昌正在办丧事,无心作战。
侯部下请求快速奇袭。
侯说:“不可以,唐天子因高昌国君傲慢,让我执行上天的惩罚。
现在赶上人家办丧事,在坟墓上奇家,不是问罪的好方式。
”于是击鼓前行,等高昌国作好守城的准备,才砍树填塞护城河,牵引撞车,摧毁城墙。
于是攻破外城,俘七千人。
进围都城。
麴文泰外无援兵,于是投降,高昌平定。
侯君集刻石表功,才返回。
侯君集支持太子谋反 但因此役侯君集部队进攻中抢掠财物、妇女。
纪律很坏,在朝廷中引起非议。
有人攻击侯君集,但李世民念他的功劳,按下不理。
侯君集自恃有战功。
因一点小过被人非议,甚至被纪律部门审查,心中不平。
这时太子李承乾有过错,害怕被废。
知道侯心有怨恨,因此找人招侯来出主意。
问稳住太子位置的方略。
侯暗示愿助李承乾一臂一力。
又说:“魏王正得势,皇上如果有诏见,不要去。
”李承乾都听从了。
侯君集是怎么死的 然而侯君集害怕有人告密,心中不安。
李承乾谋反的事终于泄露,牵连侯君集下狱,很快牵出了勋臣侯君集。
面对人证、物证,唐太宗确定侯君集参与了李承乾的阴谋。
唐太宗希望对他网开一面,群臣都说,“侯君集大逆不道,应该用国法处置他”。
唐太宗无法否决众臣的意见,只能与侯君集最后诀别,此时,大唐泪如雨下,侯君集也泣不成声,血雨腥风中走出的生死战友,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
李世民亲自审问侯,说:“我不愿刀笔吏欺辰公侯。
”侯君集不知道怎么回答。
李世民对群臣说:“侯君集于国家有功劳,我不忍心处置他。
为他向大家讨一条命,王公大臣们允许这样吗?”大臣们都说:“侯君集大逆不道,请将他按法律处罚。
” 李世民于是说:“与侯公诀别了,从今后,只有看到侯公的遗像了。
”因而流泪。
于是斩杀了侯,将其家属没入官府。
侯临上刑场,面色不变,对监斩官说:“我要造反?只是运气不好,蹉跎成这样罢了。
然而我曾为将,攻下两个国家。
你可告诉陛下,留一个儿子给我祭祀。
”李世民听了,将他妻子及一个儿子流放五岭之外。
一代将星陨落了,结束了他的荣辱一生,也许是他成功得太快?也许是他过于执着?他的不甘,让人动容,而李世民的眼泪,则让人心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魏丑夫:战国权力漩涡中的男宠与人性博弈
魏丑夫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被明确记载的男宠,其人生轨迹与秦的政治生涯深度捆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
一、身份谜团:从市井到宫廷的逆袭 魏丑夫的出身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
据《》记载,他可能是流亡贵族后裔,或仅为咸阳城中的落魄书生。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因长相酷似宣太后年轻时的初恋情人,被作为政治工具献入宫廷。
这种 替身文学 的设定,既符合战国时期宫廷斗争的残酷逻辑,也暗合宣太后对情感慰藉的深层需求。
在执政晚期,魏丑夫以 侍从 身份进入宫廷,凭借精通音律与善解人意的特质,迅速获得太后宠信。
其从市井到宫廷的跃升,既得益于个人才貌,更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对男性美色的特殊审美——不同于后世对男宠的贬低,战国贵族更看重其文化素养与情感共鸣能力。
二、权力棋局:男宠与太后的共生关系 魏丑夫与宣太后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情感依赖。
在秦昭襄王早期,宣太后通过 四贵 (、、公子悝、公子芾)掌控朝政,魏丑夫作为 隐形第五人 ,实则扮演着权力缓冲器的角色。
他既不参与核心决策,又能通过情感纽带消解太后的政治焦虑,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其在宫廷斗争中得以自保。
宣太后对魏丑夫的宠爱达到何种程度?史载其晚年将私库钥匙交予魏丑夫保管,甚至允许其参与部分外交礼仪。
这种超越常规的信任,既源于太后对青春情感的追忆,也包含着对权力延续的隐喻——当魏丑夫穿着象征秦国最高礼制的玄端服侍奉太后时,其身份已悄然从男宠转向权力符号的具象化载体。
三、生死博弈:殉葬风波中的政治智慧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宣太后病危时下令 以魏子为殉 ,将这段关系推向生死考验。
这道殉葬令背后,实则暗含三重政治逻辑:对魏丑夫过度干预政务的警告、对先王的赎罪仪式,以及通过极端手段巩固太后权威。
魏丑夫的绝地反击堪称经典政治博弈。
他通过谋士提出 人死无知 与 先王积怒 的双层逻辑,既利用战国时期流行的无神论思想动摇太后决心,又以孝道伦理迫使太后让步。
这场对话本质上是新兴思想与传统的交锋,庸芮 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久矣 的诘问,实则暗示宣太后若执意殉葬,将动摇秦国 以孝治天下 的立国根基。
四、历史镜像:男宠现象的文化透视 魏丑夫现象绝非孤例。
将之与同时期与的组合对比,可见战国男宠的两种典型模式:嫪毐代表政治投机型,最终因觊觎王权而覆灭;魏丑夫则代表情感依附型,通过精准把握权力边界得以善终。
这种差异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对男宠的双重期待——既是情感寄托,更是权力游戏的参与者。
从文化史视角审视,魏丑夫的存在挑战了传统性别秩序。
在男权主导的战国社会,宣太后公开豢养男宠并赋予其政治影响力,实则是女性统治者对性别压迫的隐性反抗。
这种 以男宠制衡男权 的策略,与后世设置 控鹤监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五、余音绕梁:历史评价的维度重构 后世对魏丑夫的评价长期陷入道德批判的窠臼,但若置于战国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其存在价值远超 男宠 标签。
他既是宣太后情感世界的投射载体,也是秦国权力结构的润滑剂,更是研究战国性别史与政治文化的重要标本。
在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坑中,学家发现多具青年男性骸骨与女性贵族合葬,这种 反传统殉葬模式 或许正是宣太后-魏丑夫关系的物质遗存。
它提示我们: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需要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转而关注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逻辑与文化意义。
魏丑夫的人生轨迹,恰似战国权力棋局中的一枚特殊棋子。
他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又在不经意间改写了历史走向。
当后世学者在竹简残片中拼凑其人生碎片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男宠的,更是一个时代对权力、情感与生死命题的终极叩问。
这种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对话,或许正是历史研究最迷人的魅力所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