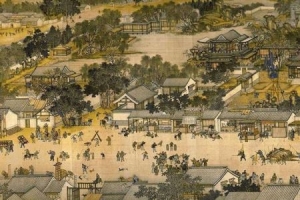抗战中的西南联大:在战火硝烟与物资匮乏中治学

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
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
图书馆用汽灯。
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
【千问解读】
刚来的时候,学校没有装电灯。

寝室里是八人一组,公用一盏油灯。
图书馆用汽灯。
偌大一个图书馆并没有几盏,因此抢座位比在电影院购票还要拥挤。
光远写道:“天未黑,馆外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门一开便向里涌,涌进门便分头向汽灯下面跑,等跑到坐定,低头一看,往往便会发现笔记本挤烂了,洋装书的硬封面挤脱了,笔记丢了。
这还是幸运的。
不幸的是出了一身汗还分不到一点灯光的人,于是便只有垂头丧气地又踏出了倚斜的馆门。
”那时,联大的学习氛围很浓。
从内地来的、从沦陷区集中上海再从海道来的,都集在这里,抱着一种希望,想学到一些什么。
那时昆明的凤翥街很热闹,那是昆明以北数县上省的驮马队驻足的地方,这些莘莘学子便与为伍,燃马粪看书。
在联大上课,课分散,教室更分散,无时不须“马拉松”。
联大学生记录道:“一课在新舍东北区,一课在后来改为女生宿舍的南天一柱,或是乾坤正气大教室,另一课也许在昆北食堂,再一课也许又得跑出大西门到现在师院去,而又一课或者又须跑进城到现在的云端中学(那时的昆中),跑到教室,工作并未完,还得抢椅子,因为座位不够,到迟一步,便只有立着听课了。
” 虽然条件艰苦而清贫,联大的课堂却是大师云集的地方。
后来成为翻译大家的许渊冲在昆中北院一号教室旁听陈寅恪讲“南北唐史研究”。
许渊冲在他的书《逝水年华》中回忆道:“他闭着眼睛,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放在膝头,不时发出笑声。
”钱锺书那时才20多岁,戴一副黑边大眼睛,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
他除了给“大一”新生开课,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
他讲课只说英语,一口牛津腔,要求学生们学习标准的伦敦音。
联大的课堂上,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各显神通,非常精彩。
有朱自清讲《古诗十九首》、闻一多讲《》、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唐兰讲《史通》、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魏建功讲《狂人日记》、冯友兰讲哲学等等。
联大不但校内名师云集,校外名人来演讲的也不少。
茅盾、老舍、范长江都来联大作过大报告;孙伏园、曹禺来作过小报告;巴金、沈从文、萧乾来参加过座谈会。
联大没有礼堂。
一些重要的演讲就安排在昆华中学北院进行,有的就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
抗战期间,学家董作宾、科学社社长任鸿隽、政治学家罗隆基、甲骨文研究权威陈梦家和长老会传教士W.H。
克拉克都被学生自治会邀请来联大演讲。
在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钱端升谈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何永佶谈英国与东亚的关系,洪思齐谈苏联与东亚的关系,贺麟谈青年与仰,沈从文、朱自清、罗常培和闻一多则探讨各种文艺问题。
抗战时期,联大在昆明为大学生提供了一块相对远离战乱与喧嚣的精神家园。
据美国学者杜易强统计,仅仅是1942年秋,一个学期下来,“国文学会和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文史论坛就推出了联大教授主讲的20多场讲座,每位演讲人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深湛的造诣”。
1941年初,昆明已屡有空袭。
到了8、9月,学校大遭轰炸,图书馆、饭厅、教室、寝室都有损坏,联大同学当时是“床床雨漏无干处”。

跑警报逐渐成了日常课程。
费孝通后来写道:“警报密的时候,天天有;偶然也隔几天来一次。
我在这些日子,把翻译《人文类型》排成早课。
大概说来,十点左右时最可能放警报的。
一跑可能有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二点钟才能回来。
所以,一吃过早点,我太太就煮饭,警报来时,饭也熟了,焖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
”有一次躲警报回来,“文化巷已经炸得不大认识了。
……哭声从隔壁传来,前院住着一家五口,抽大烟的父亲跑不动,三个孩子,一个太太,伴着他,炸弹正落在他们头上,全死了。
亲戚们来找他们,剩下一些零碎的尸体。
在哭。
更坏的一件一件传来。
对面的丫头被反锁在门里,炸死了。
没有人哭,是殉葬的奴隶。
我鼓着胆子出门去看,几口棺材挡着去路,血迹满地。
我打了一个恶心,想吐,连忙缩了回来。
……城里的轰炸从那时起一直到‘飞虎队’光临,足足有两年,着实凶恶了不少”。
在战争中,毕生的学术成果可能毁于一颗炸弹,也可能消失在一次空袭警报的混乱中。
无论什么时候跑警报,金岳霖教授都携带着《认识论》的稿子,这部稿子花了他近30年心血的成果。
躲在小山坳里避难时,他就坐在那件宝贝上,格外注意防范。
一天,空袭警报解除之后,他匆匆忙忙往城里赶。
刹那间,他意识到自己把手头的巨著丢下了,便赶紧返回原地,但书稿已经不见踪影。
事隔差不多40年后,他调侃着回忆,“很可能被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他重写了全部70万字的书稿。
战时的研究者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的。
藏有珍稀典籍的图书馆和配有最新科学设备的实验室都搁置在沦陷区。
运出的藏书和仪器要么毁于途中,要么在到达目的地时已七零八散。
从化学用品到书写用纸,基础材料的供应都很吃紧。
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1943年3月访问云,发现自然科学的每个学科都有人在简陋至极的实验室里坚持工作。
那时,战时科学研究最有成果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战时在云南开展的大量研究,尤其是理工科的项目,都是在昆明僻远的乡村进行的。
清华的无线电研究所设在大普吉,距昆明城有五六公里路。

清华的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也设在大普吉。
沈同教授在泥地瓦屋这样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
战时,数学系的华罗庚发表了20多篇论文,以他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嘉奖。
由于设备极度缺乏,实验科学的研究成果削减得最为厉害。
联大的实验物理相当薄弱。
北大的吴大猷认识到,除非中国最重要的学者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持研究的技能和精神,否则战后不可能开展学术建设。
为了维持科研水平,他开始自行设计器材,利用抢救出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同事从美国带回来的低压汞弧灯,在岗头村一个小泥屋里的临时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研究拉曼效应。
曾经留学剑桥的赵忠尧和张文裕则继续做实验研究宇宙射线。
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曾回忆,他后来的工作,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在联大时期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而他的硕士导师、毕业于剑桥的王竹溪,是昆明“最热情最渊博的教授之一”。
1945年,杨振宁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Enrico Fermi)和泰勒(Edward Teller),却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
年底,美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
“皖南事变”发生后,压抑的气氛迫使学生退出政治行动,回到课本,满足于茶馆和电影院的小乐趣;“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宣告了联大三年来活跃政治氛围的终结。
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来到中国,帮助击退了日机,基本上消除了空袭的威胁。
而就在这一年,通货膨胀开始加剧,不停地蚕食着联大沉潜研究的极其有限的资金保障。
“皖南事变”以来,三青团和群社一度热火朝天的政治辩论渐渐沉寂。
联大学生要么埋头苦读,要么泡茶馆、打桥牌、跳舞打发时间;刚开始的激情四溢,而今意兴阑珊,暮气横生。
对教授们来说,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凭着薪水养家糊口,战争岁月里在云南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相反,是沮丧失意的。
1943年,蒋梦麟校长在给当时在任驻美大使的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联大苦撑五载,一切缘轨而行,吾辈自觉不满,而国中青年仍视为学府北辰,盛名之下,难副其实。
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
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孟真之创联大之议。
”北大语言学家罗常培描绘了一幅更加惨淡的画面:“在昆明住了六年,颇有沉闷孤寂之感!……绝对的同行……偶尔写一点东西,错处没人修正,好处没人欣赏……我渐渐失去了学术重心,专以文科而论,如锡予、如觉明,都是想做些事的,一则限于经费,一则限于领导者的精力,处处都使工作者灰心短气。
”1943年5月,费正清访问昆明时发现,营养不良的“联大教授坐在太阳下喝茶,什么事都不想做”。
希望维系一个宁静学术和精神家园的联大,最终无法抗拒卷入抗战与政治的浪潮中。
1943至1944年冬天,西南地区的城市开始正式招募学生参加军事服务,驻华美军及美国人在印度训练的远征军,人数越来越多,他们特别需要译员与中方沟通。
就在“事件”爆发前,美国志愿军(即“飞虎队”,后来的第14航空队)抵达昆明时,有些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双语志愿团。
1944年4月,联大教授会表决要求,毕业班所有身强体壮的男生投笔从戎当译员。
激进的革命力量也在酝酿着。
1943年10月的一天,有个学生经过新校舍一间教室,听见闻一多高亢的声音,他朗诵了《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卫们》之后,:“我们沉醉在软弱的弦调里太久了,我们需要鼓的音乐!鼓的敲击使我们想到战斗。
什么是鼓的时代?战争的时代!” 随机文章恐惧魔王迪亚波罗,勾引王子占据身体和灵魂(天堂最大敌人)盘点冥界四花都有哪四种花,彼岸花/曼陀罗花/罂粟花/夹竹挑(邪门)扎西德勒是什么意思啊,欢迎/吉祥如意意思/疑似源于18000年以前诺亚方舟遗址是真的吗,上帝毁灭罪恶的人类/方舟造船救出七公七母美俄让中国不要碰月球,月球上存在神秘势力阻挡人类探索月球迷案在线 mazx.cn本站内容大多收集于互联网,内容仅供娱乐,并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果本站内容侵犯了您的权益,敬请联系网站管理员,我们将尽快回复您,谢谢合作!
孤舟浮江,诗心映世:马周诗句中的寒微之志与家国情怀
这位以政论文章闻名史册的能臣,仅存的两首诗作却成为解读其精神世界的密钥,在山水意象与人生哲思间,勾勒出初唐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
一、孤舟映日:寒微境遇中的诗意突围 《凌朝浮江旅思》开篇 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 ,以晨曦初照、孤舟漂流的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羁旅图景。
这种 孤舟 意象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马周早年困顿生活的隐喻——他出身清河茌平寒门,少孤贫而好学,精研《》《春秋》却久困场屋。
诗中 山远疑无树,潮平似不流 的视觉错位,恰似其怀才不遇的生存困境:远山隐于雾霭,暗喻仕途渺茫;潮水看似凝滞,实则暗涌流动,隐喻着诗人内心对机遇的渴望。
这种寒微书写在 岸花开且落,江鸟没还浮 中达到极致。
花开花落的瞬间轮回,与江鸟沉浮的动态捕捉,既是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更是对人生无常的哲思。
北宋张耒在《马周》诗中 布衣落魄来新丰 的描述,恰与此诗的孤寂意境形成互文,共同勾勒出寒门士子在盛世中的精神困境。
二、邓林栖枝:知识分子的精神突围 马周现存另一残句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虽仅十字却振聋发聩。
此句化用《·逍遥游》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的典故,却翻转出新的意蕴:当邓林(神话中昆仑山神木)般的机遇近在咫尺,诗人却选择 不借 的傲骨。
这种选择绝非消极避世,而是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精神突围——贞观十一年,他以《陈时政疏》直谏唐太宗 积德累业,恩结人心 ,展现出比借枝栖息更深远的政治抱负。
这种精神特质在《凌朝浮江旅思》的结尾 羁望伤千里,长歌遣四愁 中得到升华。
面对千里羁旅的哀愁,诗人选择以诗长歌消解,而非攀附权贵。
这种 不借枝栖 的独立人格,与同时代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的悲愤形成对照,更显其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三、政论诗心:双重文本中的士人担当 马周的诗歌与其政论文本构成奇妙的互文关系。
在《陈时政疏》中,他痛陈 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 ,这种以民为本的忧思,与《凌朝浮江旅思》中 羁望伤千里 的悲悯一脉相承。
其政论文 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 的论述,恰可视为 长歌遣四愁 的另一种表达——将个人愁绪升华为家国担当。
这种双重文本的创作特征,在初唐文人中颇具代表性。
马周既能在《请劝赏疏》中提出 劝农务本 的具体政策,又能在诗中保持 岸花开且落 的审美距离,这种 入世 与 出世 的平衡,使其成为研究唐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典型样本。
四、历史回响:寒微之志的永恒示 马周诗句在后世文人中引发持续共鸣。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的禅意,与 潮平似不流 的静观哲学遥相呼应;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的超脱,暗合 长歌遣四愁 的精神境界。
这种跨时空的共鸣,源于寒微文人共通的生存体验——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精神独立,在困顿境遇里坚守理想主义。
在当代语境下,马周诗句的价值更显珍贵。
当现代人面对 内卷 困境时, 何惜邓林树,不借一枝栖 的傲骨,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坐标;当社会焦虑蔓延时, 岸花开且落 的哲学思考,为浮躁心灵注入清凉剂。
这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正是经典诗歌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
从孤舟漂流的寒微书生到位极人臣的贞观,马周的人生轨迹恰似其诗句的双重变奏——既有 春水送孤舟 的凄清,亦有 一语君王见胸臆 的豪迈。
他的诗句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文学注脚,更是初唐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镜像。
当我们在苏州河畔诵读 太清上初日 时,听到的不仅是千年前的江涛拍岸,更是一个时代寒微之士的灵魂回响。
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或许正是诗歌给予文明最珍贵的礼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魏丑夫:战国权力漩涡中的男宠与人性博弈
魏丑夫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被明确记载的男宠,其人生轨迹与秦的政治生涯深度捆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印记。
一、身份谜团:从市井到宫廷的逆袭 魏丑夫的出身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
据《》记载,他可能是流亡贵族后裔,或仅为咸阳城中的落魄书生。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其因长相酷似宣太后年轻时的初恋情人,被作为政治工具献入宫廷。
这种 替身文学 的设定,既符合战国时期宫廷斗争的残酷逻辑,也暗合宣太后对情感慰藉的深层需求。
在执政晚期,魏丑夫以 侍从 身份进入宫廷,凭借精通音律与善解人意的特质,迅速获得太后宠信。
其从市井到宫廷的跃升,既得益于个人才貌,更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阶层对男性美色的特殊审美——不同于后世对男宠的贬低,战国贵族更看重其文化素养与情感共鸣能力。
二、权力棋局:男宠与太后的共生关系 魏丑夫与宣太后的关系远非简单的情感依赖。
在秦昭襄王早期,宣太后通过 四贵 (、、公子悝、公子芾)掌控朝政,魏丑夫作为 隐形第五人 ,实则扮演着权力缓冲器的角色。
他既不参与核心决策,又能通过情感纽带消解太后的政治焦虑,这种微妙的平衡使其在宫廷斗争中得以自保。
宣太后对魏丑夫的宠爱达到何种程度?史载其晚年将私库钥匙交予魏丑夫保管,甚至允许其参与部分外交礼仪。
这种超越常规的信任,既源于太后对青春情感的追忆,也包含着对权力延续的隐喻——当魏丑夫穿着象征秦国最高礼制的玄端服侍奉太后时,其身份已悄然从男宠转向权力符号的具象化载体。
三、生死博弈:殉葬风波中的政治智慧 秦昭襄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宣太后病危时下令 以魏子为殉 ,将这段关系推向生死考验。
这道殉葬令背后,实则暗含三重政治逻辑:对魏丑夫过度干预政务的警告、对先王的赎罪仪式,以及通过极端手段巩固太后权威。
魏丑夫的绝地反击堪称经典政治博弈。
他通过谋士提出 人死无知 与 先王积怒 的双层逻辑,既利用战国时期流行的无神论思想动摇太后决心,又以孝道伦理迫使太后让步。
这场对话本质上是新兴思想与传统的交锋,庸芮 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久矣 的诘问,实则暗示宣太后若执意殉葬,将动摇秦国 以孝治天下 的立国根基。
四、历史镜像:男宠现象的文化透视 魏丑夫现象绝非孤例。
将之与同时期与的组合对比,可见战国男宠的两种典型模式:嫪毐代表政治投机型,最终因觊觎王权而覆灭;魏丑夫则代表情感依附型,通过精准把握权力边界得以善终。
这种差异折射出战国时期贵族对男宠的双重期待——既是情感寄托,更是权力游戏的参与者。
从文化史视角审视,魏丑夫的存在挑战了传统性别秩序。
在男权主导的战国社会,宣太后公开豢养男宠并赋予其政治影响力,实则是女性统治者对性别压迫的隐性反抗。
这种 以男宠制衡男权 的策略,与后世设置 控鹤监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五、余音绕梁:历史评价的维度重构 后世对魏丑夫的评价长期陷入道德批判的窠臼,但若置于战国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其存在价值远超 男宠 标签。
他既是宣太后情感世界的投射载体,也是秦国权力结构的润滑剂,更是研究战国性别史与政治文化的重要标本。
在坑出土的青铜水禽坑中,学家发现多具青年男性骸骨与女性贵族合葬,这种 反传统殉葬模式 或许正是宣太后-魏丑夫关系的物质遗存。
它提示我们: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需要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转而关注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为逻辑与文化意义。
魏丑夫的人生轨迹,恰似战国权力棋局中的一枚特殊棋子。
他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又在不经意间改写了历史走向。
当后世学者在竹简残片中拼凑其人生碎片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男宠的,更是一个时代对权力、情感与生死命题的终极叩问。
这种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对话,或许正是历史研究最迷人的魅力所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